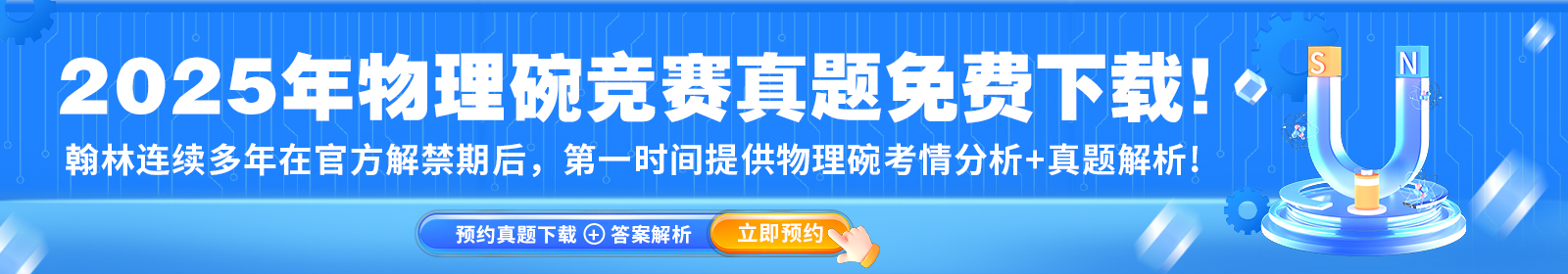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Daniel Negreanu 自述:“人,数字,竞争”
先说说什么是SPR
SPR全名为Stack to Pot Ratio,它是一个比值,用剩余(有效)筹码除以锅里筹码得来的数字就是SPR。使用SPR的语境一般在翻牌前动作完成后,翻牌行动开始之前衡量。
SPR就是两个数字的比例。这没有什么神奇的。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甚至连工具也不算,就是一个衡量方法。即使不用SPR,我们也会大致地说:小锅、大锅、我面前筹码很少、我的筹码还挺深等等起到类似作用的语言,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跟SPR可以类比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温度计。温度计是用来衡量温度的。在温度计发明之前,人们肯定有很热、很冷、烫手、冰凉等等一系列描述冷热的词汇,也不会因为没有温度计就不知道出门穿什么衣服,或者烧水烧不开。
然而温度计发明之后,温度被量化,成了数字。这貌似也没啥大不了的,其实不然。
首先,交流方便多了。天气预报可以说25度,你就可以知道该穿什么衣服了。两个地方的人见面,不知道谁那儿热,都说自己那里凉快。拿温度计一测,一个20度,一个18度,这下毫无争议,问题解决。当然,温度计得是标准的。
其次,量化温度能帮助产生很多新产品,比如说温控冰箱、暖箱。只知道冷热不知具体数字,我们就永远不会做出把温度定到-18C来冷冻海鲜,4C来冷藏水果。
德州扑克之所以难,就是因为绝大多数选择都是双向的:我们既要担心自己的牌榨取不到不够价值,也要担心一旦对方的牌大时我们输的太多。如此瞻前顾后,大量耗费脑细胞,且效果还不一定好。
Daniel Negreanu 自述:“人,数字,竞争”
我很难准确的指出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以扑克为生的,但是要是回溯以往的话,在我童年时期还是有一些关键的时刻导致我走向职业道路的。
在我5岁的时候,爸妈带我和我哥哥去逛商场,我就像其他小孩那样盯着路人看啊看的。但是和别的小孩不同的是,我还会试图观察别人在想什么,就像现在我也会观察对手一样,我小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
我记得当时有一对情侣在吃午饭。女方很漂亮,男方看起来很有钱,而且很爱那个女的。因为我发现男方非常关注女方的一举一动,他一直微微靠向女方,而且想一直握着她的手。但是这个女的就不一样了,她根本不爱那男的。男方每次示爱,她的眼珠都会乱转,一副非常厌烦的样子。
过了几分钟,他们的一些朋友过来了。突然那个女的眼睛一亮。她的右腿微微像另外一个刚刚坐下来的男的倾斜。我当时只有五岁,但是我记得我对自己说,她跟着这男的只是为了钱,她不爱他,她喜欢的是另外那个刚坐下来的男的。
尽管刚刚那只是一个简单的读人,但是对于一个五岁小孩来说也不算太简单了。从那时开始,每次去商场我都会干这种事。我简直对此无法自拔,我就是喜欢观察被人,试图读出他们的特点。我做的这些事恰好是扑克桌上的一项完美的训练。这跟你打牌的时候做的事是一样的,试图走入别人的大脑,探明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我生长在多伦多一个传统的欧洲风格的家庭。我父亲是个电工,母亲是罗马尼亚人,在家做全职主妇,照顾孩子们。我有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我们几乎什么事都吵,他比我高比我强壮,负责解决所有事,而我只能帮忙打打电话。
除了观察别人,我童年时期另一大爱好就是数字。我玩电脑和别的小孩不同。当时有个游戏叫RBI棒球,我记得我玩这个游戏会追踪游戏数据。如果一个球员的击中次数是4/11,我就会算出他的击中率是35.4%,当时的游戏不会为你记录这些,但是我会自己记录。我妈妈当时经常会奇怪我弄这么多纸写写画画是在干什么。当时我用来记录的纸摆满了整个屋子。
我对人,数字,竞争的痴迷最终带我来到的扑克世界。我幼年时期并没打过牌,我第一次打牌是朋友在台球厅带我打的。有一次台球赛过后我被邀请去了一个人家打CASH,我带了10刀和半打啤酒过去了。他们会打很多乱七八糟的项目,第一次不出意外的,很快我就输掉了这10刀,然后我就开始坐在一边为他们加油助威了。后来每周去打牌变成了常规项目,由于我的竞争天性,我开始试图找到游戏的诀窍。我发现有个亚洲人John Sato几乎每次都会赢钱,我发现他每晚几乎就玩那么四五手牌,我好奇为什么不参与游戏却能赢钱。后来我注意到他每次入池都是超级大牌,而其他玩家似乎并不在乎这点,每当Sato入池他们就应该赶快跑掉。
我在Sato这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没牌别入池。要有耐心,等待好牌。当我学会去打很少的手牌时,情况开始好转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的扑克局被敲响了警钟。一个又圆又胖,喷着古龙水,浑身珠光抛弃的意大利长发男Benny加入了游戏,并且完全掌控了整个局面。他每次下注都很重,他会主动攻击其他人,累积筹码,那天晚上他赢了600刀走,这是我们见过最大的胜利了。Benny的疯狂侵略风格主宰了整个牌桌。所以到此我了解了两个风格,一个是Sato的紧石头风格,一个是Benny的超级大炮,一直砸对手直到对手投降。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