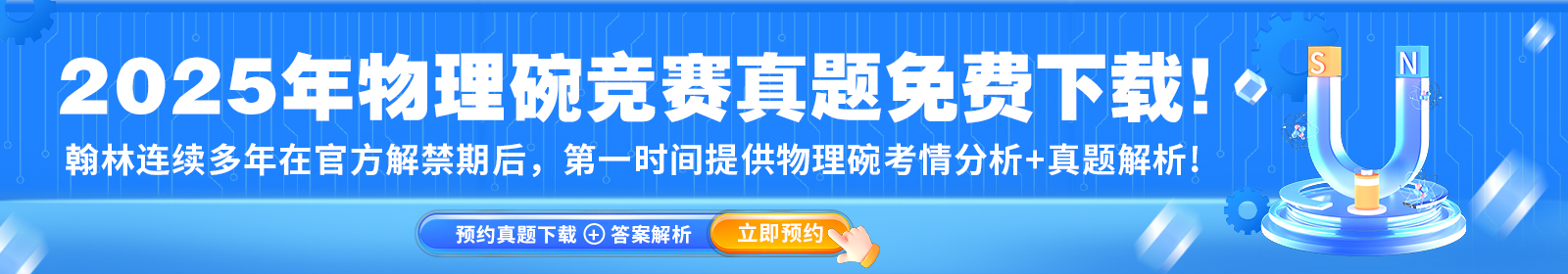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自闭症儿子成长记:美国公立学校如何支持特殊儿童教育
儿子
我的小儿子Quentin有自闭症。更确切地讲,他有艾斯伯格综合症。不仅如此,Quentin还有情绪失调症,这是因为大脑或精神疾病极少只限于一种。两种疾病交织,带来了诸多人际交往方面的严重问题,而情绪管控能力的极度低下,是迄今为止病症最为突出的方面,也最妨碍他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正常功能发展。
人们常常问我,你是什么时候知道Quentin有问题的。我的回答是,几乎是从一出生。Quentin一出生就在医院不停地嚎哭了十多个小时。他能走路之前,我们的生活只有经历过“天皇皇,地慌慌,我家有个搅夜郎”的家庭才能理解(后来回想起来,这些问题都与感统和情绪失调有关)。与此同时,Quentin天性喜欢逻辑和规律,也有超凡的记忆力。一岁半发现哥哥在学习字母和发音时,他很快就自学了所有规则。到了两岁,他已能认识并拼写几百个字,也能读一些儿童书。然而,三岁半左右,Quentin却不能回答简单的“是”与“不是”问题,因为语言对他只是自我娱乐的工具,不存在交流的功能。当然,因为Quentin很聪明,当我们想办法帮他建立了言辞与交流之间的联系时,他的表达功能很快就赶上了同龄人。我还记得Quentin坐在哥哥拆开的一堆玩具零件里,说出的第一句相对完整的话,“My brother took [them] apart”。
在言语能力取得进展的同时,Quentin的感统失调问题越来越显著。在他诸多奇怪的动作和行为中,最让我心痛、焦虑的是他经常拍耳朵,而且越是人多嘈杂,他越拍得频繁。医生检查,耳朵和听力都没有问题。而且Quentin只会学习,不会玩,对玩具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感兴趣,只会把什么东西都排成一行。与其他孩子在一起,Quentin从来只做平行“玩耍”,即各玩各的,彼此之间没有来往。Quentin也从没像哥哥一样,用手指指过东西给我们或任何人看(用术语讲,这叫不会共享注意力(shared attention)),与人的眼神交流极其有限,很多时候根本不知别人讲话的对象是谁,自己讲话也不在乎对象是谁。这些都是经典的自闭症特点。这个时候,我已有了一些自闭症的初步知识,带他去看儿童发育专家,诊断是轻度自闭。然而,几个月后,当儿子智商被测定为170,专家摘了他自闭的帽子,因为10多年前,人们对自闭的理解还不够,以为自闭儿童不可能有超常智商,超常智商儿童不可能自闭。另外,做感统的治疗师一来和儿子做活动,儿子很感兴趣(作为一个幼儿,这个世界充满让他好奇学习的东西——除了人之外),所以他注意力异常集中,从而掩盖了他的很多问题。
帽子摘掉与否,作为母亲,我确信他有自闭症,而且带着两个幼儿的日子很不易,因为在任何公共场合,我都在追Quentin——他没有任何危险感,总是到处奔跑,也从不回头看大人有没有跟他。因为他随时都有出问题的危险,让人不能有任何懈怠。记得一个冬天,我带两个儿子去儿童博物馆,老大老老实实在身边等我买票。我买了票,一回头,老二已了无踪影。周围的妈妈们都跟我一样紧张,分头和工作人员帮我找了半个小时,才发现老二正在他喜欢的垃圾分类箱那里一边拍耳朵,一边很投入地玩,对周围的人、事浑然无觉。又有一次,带两个儿子去一个玩具店。Quentin用玩具制造了那么多噪声(非常奇怪的是,虽然儿子很怕周围环境中的噪声,他自己却喜欢制造种种噪声),我们被从玩具店友好地“赶”了出来。
到了Quentin上学的年龄,因为我们当时所在城市公立学校名声不好,也因为我当时对公立学校不经了解就存在的偏见,再加上他感统失调问题,觉得公立学校不是好选择,想让Quentin上哥哥当时上的一所大学教育系附属试验小学。小学虽然学位有限,在校学生的弟妹却是给予优先考虑的。然而,Quentin去学校访问,行为乖张,随处乱跑乱拿东西,根本不听老师的话,极具破坏力。校长有些难为情地拒绝了我们。我们转而申请一所蒙台梭利学校,该校校舍是在安静住宅区里的一所两层楼民居,3岁到3年级只有70多个学生。Quentin超常的阅读和数学能力,使他在访问时很受老师们赏识,所以被接受。在这所学校,感谢老师们的爱心和耐心,头两三年Quentin的问题,比如他会因别人不觉得任何好笑的事情,笑得没完没了,扰乱课堂秩序,学校都还能应付。二年级是相对最顺利的一年,但Quentin总在咬胸前的衬衫,那一年穿过的衬衫,脖子下边的地方都被咬穿咬烂。这一年我记忆最深的还有一件事。暑假我带Quentin和哥哥去哈佛和MIT校园玩。回家路上,地铁在一站停下后,等了几分钟还是不动,Quentin突然非常愤怒,我的任何解释、劝说都无济于事。后来广播里通知,说前边车站发生了火灾,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我原本以为知道了原因后,Quentin会安静一些。相反,他像发疯一样从车上奔到月台上,诅咒世间对他的不公,发誓要把火车砸毁。我在月台上追赶他,斥责他,他愤怒地把我推搡个趔趄。地铁一开动起来,他马上就安静下来,过一会还为在车站的行为向我道了歉。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偶尔的一次情况,其实这是他后来几年里情绪障碍持续恶化的一个开端。
到了三年级,即蒙台梭利学校最高的一个年级,我开始不时接到学校的电话,报告类似上述行为。Quentin对花生严重过敏,每次老师们为了谨慎,不让他吃有可能接触到花生的零食,他都会愤怒得在学校大哭大闹,有时又悲伤得哭泣,有时受到老师批评则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之类的话。有一天,他去卫生间,不知为什么居然让水龙头的水无尽地流,直到整个一楼地板都被水淹。等我到了学校,平日里宽厚、友好、放松的校长脸色铁青——对于一所经济并不宽裕的小学校,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第二天再看见他,我很悲伤地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很多。问儿子为什么不去关水龙头,他回答不出来,而且脸上还奇怪地笑。
校长和老师们虽然很快原谅了儿子,但他从该校三年级毕业后的就学成了问题,与此同时,经常遭我严厉批评的Quentin情绪愤怒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并开始指责我不爱他,辱骂我,或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杀死我”。虽然还是不太愿意接受Quentin有精神疾病这一现实,我开始给儿童精神医生打电话,而每个医生都至少要6个月后才能接受新病人。有一天早上,Quentin醒来后行为极端异常,一会要躲到床下,一会要躲到衣橱里,却对我说不出原因。在儿童医院的急诊室外等待时,他想去自动售货机买吃的,东西出来时却被卡住,引发了他火山爆发一样的狂怒,医院几个工作人员才把他控制住,并通过注射镇静剂才让他得以安静。在随后和医生的交谈中,我们才知道他在一个噩梦中发现自己忘记了学到的所有东西,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才决定到处躲藏。医生还问儿子是否有过自杀念头、是否曾试图伤害自己或别人等问题。我当时觉得这些问题非常不恰当,觉得这有可能把儿子本来没有的念头放到他头脑中。尽管我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医生还是决定儿子应当马上被送去儿童精神病院得到评估和治疗。事后我对这位医生非常感激。正是她的坚持,使Quentin得到了紧急治疗,也使我们有缘认识了H医生。从Quentin 4年级开始,H医生一直就是他的精神医生,成为了支持Quentin和我们全家这一专业网络的重要成员。关于精神药物和H医生的作用,我会专门再写一篇文章介绍。
就是在上述危机背景下,在我们申请过的所有私校都拒绝了Quentin的情况下, 我们决定搬到一些老师和家长推荐的麻省一个镇上,因为该镇特殊教育名声很好。 这个时候,我已充分意识到每个艾斯伯格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因为在我大量阅读过程中接触到的所有儿童案例,似乎没有一个很适合Quentin。虽然学校名声好,而且我作为潜在学生家长访问镇上一所小学时,得到了校长友好坦诚的对待,并参观了学校里的自闭症项目,但我很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应对Quentin:一方面智商远超出同龄人,很喜欢有挑战性的智力活动,所以需要文化课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从不考虑别人,对正常孩子来说蚁穴一样的任何小事(比如电脑出点故障)就能在他身上马上点燃剧烈的反应,而且对与别的孩子交往没有任何兴趣。我们在这所小学附近买了房子,8月初搬到了镇上,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公立学校经历
麻省这家小镇,人口18,000,一共有5所公立学校,其中小学3所,初中1所,高中1所。开学前两三天,我访问过的小学校长跟我联络,约Quentin和我与镇上公立学校系统学生服务主任Steve见面(学生服务其实就是特殊教育)。Steve50多岁,瘦瘦的,中等身材,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文质彬彬,像个学者。和他一起的还有学校系统的行为问题专家。一见面,Steve就先与Quentin握手介绍自己,并试图与他交谈,儿子很粗暴愤怒地回答两句,就走开了。从多方面来说,我都很尴尬。一是儿子行为,一是作为多年来一直交学费,现在却搬到镇上来免费利用教育资源、尤其是特教资源的家长,骄傲很受打击。所以一开始就说,如果教育Quentin真是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我肯定不会来镇上成为大家的负担,并情不自禁地掉眼泪。Steve拍拍我的肩膀,安慰说,你们绝对不是镇上的负担,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是他和你们的权利,我们就是为孩子和家长服务的。听我简要介绍儿子情况后,他说镇上另外一所小学专门有个针对艾斯伯格孩子开设的项目,Quentin更适合去那里,而且学校系统会有给特教学生提供的免费车辆,接送他上下学。30分钟后,我们在那所学校会面,Steve把我介绍给了项目负责老师Ana。Ana待我和Quentin如重要客户,告诉我们因为Quentin的障碍,学校将给他配备一位教学助理,陪他在正常课堂里上课。如果Quentin有言语行为不当之处,助理会提醒他,需要时带他出去走走,必要时则带他到特教教室单独上课或学习。我告诉Ana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到学校来陪儿子上课。她说完全没必要,这是我们特教团队的工作。回到家里,我和先生谈起一天的经历,觉得真是一到镇上就受到了这个社区的拥抱欢迎。
按照联邦残障人保护法和残障孩子教育法,公立学校必须为每个孩子,无论有无障碍,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障碍,无论有无行为问题,都提供恰当的、高质量的教育。这一要求,意味着所有有障碍、有疾病的孩子不但免费上公立学校,而且在可能情况下都能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如果不是在校全部时间,至少是一部分时间。我曾有机会陪同国内教育工作者访问过美国不少学校,考察美国的特教,目睹患有严重疾病和极度残障的孩子们,被护士、助理推着轮椅,参加课堂活动,或只是为了能和正常孩子再待一段时间。从法理上,这一要求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孩子们需要和同伴们在一起成长,有障碍孩子可以以正常孩子为模范,而正常孩子也可以从与有障碍孩子交往中受益。从实际角度,疾病和障碍使得这些孩子的家庭难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不论社区和社会多么宽容。举例来讲,Quentin有一度会在交通绿灯突然变为红灯时暴怒,致使他和我们几乎无法出门,连不用与人打交道的活动都无法去做,整个家庭都觉得非常孤单。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就成了孩子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与人交往的地方。
残障人保护和教育法律,通过残障人士和家庭多年推动而通过,在实施过程中也由于他们的努力(有时通过法庭诉讼)而得以进步和完善。目前虽然正常孩子的义务教育是幼儿园到12年级,对残障孩子的义务教育则是从0到21岁,即残障孩子一得到诊断,就可以得到公立学校的全套服务,包括护理、教育、交通,以及就业准备。讲到交通,为了保证残障孩子上学,公立学校不但免费提供从家门到学校的接送服务,还要保证接送车辆配备有各种安全设施,以保证孩子们使用的辅助设施和医疗设备等能在车上被栓牢。有意思的是,在我们镇上,正常孩子乘坐校车是要交年费的,而残障孩子接送则是免费的。在一定意义上,残障孩子可以说是成了享受特权的一个群体。而美国的共识是,这种特权是应当的,是社会对于他们遭受大自然母亲给予的不公平对待的弥补。
残障孩子教育的核心是IEP(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即个人教育计划。这一计划在每个学年开始,由家长和教师团队(包括文化课老师、学校特教协调人、特教负责老师、学校心理学家、行为问题专家、言语/物理/职业治疗师等)共同讨论制定,包括孩子目前诊断、言语/行动/智力/行为/社交技能等评估报告,根据孩子障碍和家长希望开发的的教育总目标、年度总目标和各功能区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等。整个学年期间,学校会定期给家长书面汇报孩子进展,必要时也会与家长约时间,由相关老师与家长开会交流信息和讨论,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因为Quentin的障碍在于他的自控和社交能力的缺乏,我们搬到镇上后,他的IEP重点关注这些领域。4到5年级,Quentin发生过几次大的由暴怒到试图攻击老师的行为。如果有必要从身体上控制他,Ana都会在采取行动之后马上发电邮给我们,告知事情原委。暑假期间,为了保证Quentin学到的能力不退后,学校专门给他免费配备助理,使他能免费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这些夏令营对于正常孩子都是收费的)。
Quentin小学毕业之前,学校安排了他去初中参观,介绍他认识了初中特教负责老师和协调员,并安排了过渡会议,把家长、小学和初中特教团队组织在一起,分享Qunetin的长处和问题等。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初中是孩子们最顽劣的时期。我有一次和一位教初中科学多年的老师聊,听到了以下充满爱心的形象比喻:
“6年级学生进来时,还是很可爱的孩子,到了7年级,他们就开始在地下挖坑,身上沾满了污泥,而且坑越挖越深,他们也随之成为在这个深坑里的非人怪物,让成年人难以理解;到了8年级,他们慢慢从这个深坑里爬出来来,逐渐成了负责任的大孩子。”
在Quentin身上,这已不再是比喻,而是对现实的描述。虽然6年级他也有过诸多问题,7年级一开学,他在学校和家里的有些行为,像恶魔附身一样,不能控制,也无法解释。Quentin不是没有是非观念,因为过后对这些行为总是很羞愧,而他的这种羞愧虽然有时以道歉表现,更多时候则是一旦我们偶尔提及他的行为,他就很愤怒,因为他不想被一次次提醒那些非常羞耻的经历,而他自己似乎的确没有能力在当时控制自己。他能在正常课堂待的时间越来越少,老师一讲课,Quentin就开始发一些奇怪的声音,或说一些奇怪的话。有时老师在板书,Quentin走上去把板书内容全部擦掉,并对此很得意。助理带他到特教教室,他把教室墙上所有东西都撕摔下来,而且常把老师的咖啡倒到地上,还会对老师说些威胁甚至残酷到令人发指的话,并出手打人。不但如此,越是文化和道德的禁忌,他似乎越受吸引。比如有一度他对二战和纳粹非常感兴趣,会在学校犹太裔孩子的书本上画纳粹党标志,还会时不时在学校走廊做纳粹党人敬礼的动作。如此行为,如果发生在正常孩子身上,会有仇恨罪嫌疑,学校会请镇上警察介入。尽管老师们想尽办法,最终经过我同意,把镇上警察请到学校和Quentin交谈,希望能有些效果,但Quentin的行为都没有好转。有一次,当所有人都无法管住Quentin,事态已到了需要校长介入的水平,我接到电话到学校去,发现Quentin像无赖一样,平躺在地上,校长声音低沉,没有任何指责批评的语气,试图与他交谈。校长知道Quentin喜欢动脑子,问了他一个数学问题,吸引了他注意力两分钟。但给出答案后,Quentin又开始或哈哈大笑,或向校长吐唾沫。类似事情发生后,校长和我们都成了熟人。校长有一次跟我们说,能不能让Quentin每天上学带上旅游鞋,这样他可以带Quentin每天早上去跑步,也许消耗一些他的体能能帮他安静下来。
7年级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阶段。学校和我们频繁联络开会,当然每次开会时间都要看我们方便,而且从老师到校长到全镇教育系统心理学家,从没一个人让我们觉得是被召去受责备的感觉。相反,我们作为父母,是Quentin教育团队中平等和重要的人员,我们分享的信息和建议都被耐心听取。不但如此,因为我们积极与学校合作,很受整个团队和学校的尊重。在最困难的时候,当我作为母亲觉得绝望、几乎要放弃时,Quentin的老师们强调的总是他的长处:他电脑一样的记忆力和知识、他自学和研究能力、他有时的幽默、他对课堂讨论的贡献等等。最后经我们同意,学校决定不再让他去正常课堂,而是给他一个单独的小教室,由文化课老师和助理给他上课,并使用ABA奖励方式,鼓励他朝着能在每个课堂上不出任何问题地待5分钟、10分钟、15分钟的目标逐渐努力。因为Quentin很厌烦社交技能课(他已能背出社交技能课的所有内容。他的问题不在于不知道社交规则,而是做不到),常用言词侮辱他的社交技能老师,老师决定与他玩他喜欢的游戏,从而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从7年级后期开始,有关他的会议也会邀他参加,从而让他对自己的未来有发言机会。
7年级底,Quentin在全校《国家地理杂志》知识学术活动中名列第一,老师们都为他自豪,因为这不光表明了他的地理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定的自控,才能遵守学术活动规则。作为学校第一名,Quentin有资格参加全州初中组学术活动。我们对此很担心,但老师和学校却认为他天经地义地应当代表学校。学术活动一共有104位参赛者,分组比赛中,我们亲眼目睹了Quentin需要多么努力才能不抢着答题。分组赛结果,6位学生答对了全部问题,22位学生只答错了一道,Quentin属于其中。决赛只要10人,所以这22个孩子得竞争4个席位,Quentin最终被刷了下来。
这是Quentin初中毕业时我在微信上发的一个帖子:
“To belch=打嗝, a belcher=打嗝的人
要是你是个初中男生,你的老师碰巧姓Belcher……
要是你不但是个初中男生,你还有艾斯伯格综合症和其它障碍……
镇上初中的Mrs. Belcher,教过我家两个儿子英文。老大厚道有礼,对老师的名字笑一笑之后,再没说过什么。
老二7年级一认识Belcher老师,就在课堂、学校和家里动不动拿老师的名字开心。不但如此,他给作为他辅导员的Mrs. Belcher、其他老师和校长创造了很多难以应付的问题,使得我家在初中都是名人。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Mrs. Belcher成了他最愿意合作的人。Mrs. Belcher有两个已成年的儿子,教初中多年,不但很会应付顽劣的7年级学生,而且真正爱他们、理解他们。我曾看到过她在校车上和孩子们平等的交流和嬉戏,很感动……几乎每个人都说,Mrs. Belcher和儿子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使他在她的课堂上表现更好。”
放假时Mrs. Belcher送给了Quentin一本名为《数学的奇怪历史》书,在书的扉页上,她写了
“What do you buy for the person who knows so much? A curious history book! Hope you like it and learn some fun math facts!”
(给一个有这么多知识的人能买什么呢?一本奇异史书!希望你喜欢并能从中学到有趣的数学事实。)
给在Quentin的卡片上,她这样写道,
“Quentin,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set your mind on doing. Good luck in high school.”
(只要是你想做的,你都能做到。祝你在高中好运!)
另外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多年来有障碍孩子和正常孩子的融合教育,使多样性和宽容已深入人心。有障碍的孩子,在学校一般易成为受欺负对象,或欺负别人。尽管Quentin言语和行为怪诞(比如,有时候Quentin和我去镇上湖里游泳,碰上他的同学,孩子们都会打招呼,而Quentin不但不理他们,而且会很紧张地捂着耳朵逃走;在家里,我们很难从Quentin嘴里掏出任何有关同学的信息,似乎这些都是绝密信息),老师们告诉我们,他在做小组项目时从没缺过合作伙伴。有一次,我曾作为家长陪同,和Quentin班级一起在一个岛上做团队建设野外活动两天。两天里,有几个男孩子做什么事情都很自然地拉Quentin一把。有时Quentin发表我认为的奇谈怪论时,我不好意思,试图阻止他,孩子们却会说,让Quentin说,我们喜欢听,丝毫没有取笑他的任何意思。
对于Quentin情况的好转,我们很怕是一时的。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能否顺利,我们忐忑不安。8年级底,我们认识了他高中特教负责老师Megan。为了保证Quentin的好转能持续,也为了暑假他能有除了家以外的地方去(我们曾花了不少钱,试过两个专门为艾斯伯格孩子开办的夏令营,两次都是很失败的经历),Megan建议他参加高中为障碍孩子开办的每周两次、每次3个小时、时长6个星期的夏令营。Quentin因为过去夏令营的失败经历,开始极力反对,但最后做出让步,尽管每次回来都说夏令营的坏话,说和他在一起的孩子低能、无聊乏味。这个时候我会提醒他这么多年里这么多人对他的爱和耐心,希望他对别人也能效仿同样的宽厚。让我惊奇的是,这次Quentin居然没有反驳我。
高中前的整个夏天,Quentin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平稳情绪,并开始做一些以前从未感过兴趣的事情,比如他不再拒绝读小说,而且我们自Quentin出生以来,第一次能在电视机前共同观看故事片(此前Quentin感兴趣的只是记录片)。碰到不顺心的或意想不到的事,Quentin似乎也不再反应激烈。自小学3年级起,我们全家第一次能一起出门玩半天,而不必担心他会因为意想不到的问题发怒。夏末Quentin发现了流行音乐,开始听很多流行歌曲,并开始研究流行音乐史。9月份开学,我们每天期待学校会给我们发邮件,传达他在学校的不良行为。出乎意料的是,每次接到的都是表扬,而且Quentin上学很积极——一部分因为高中课程比较有意思,一部分因为他的助理和老师们都能与他评谈音乐。他跟同伴的交往仍然极少,但音乐给了他与很多成年人共同的话题。10月我们第一次到高中,参加了有史以来最简短的IEP会议。随后不久,Megan 产假休完,一返校就发电邮给我,询问我希望多久和她联系一次,并把手机号码给了我。儿子每次做了好事或有进步,她都会发电邮或短信与我们分享。
今年1月底,Quentin IEP进展报告有以下量化数字:
报告中还说,Quentin在管理不该说的话题方面取得了进步,对于具争议性的话题,他不再像以前冲动性甚至强迫性说出,而是会有克制。期中考试前,他主动向老师提出,考试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而不是在大课堂上,这样他需要休息期间不会影响别人。他还去找老师,提出有一门选修课不适合他的学习方式和兴趣,要求转到“电子音乐欣赏和创作”去。
我最近接到了Megan一个邮件,告诉我Quentin和学校另一个艾斯伯格孩子之间有些交往,两人有时会一起吃午饭。这是过去四五年里第一次我们听到这样的好消息。Megan把孩子母亲的电话给了我。我们已经约好这个周末见面。
一个母亲的成长与反思
养育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孩子,家庭、学校、社会都面临很多挑战。Quentin的成长历程中,最糟糕的时期,我们和学校都是处于不断应对危机状态,而最好的时期,也是磕磕绊绊地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Quentin在成长,我作为一个母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自闭症孩子的父母都说,这一过程使自己成了更好的人。我也不例外。
我的先生有一次感叹说,Quentin是我们的耐心老师,是他教了并不断考验我们的耐心。的确如此。Quentin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起初,一部分因为对他没有深刻的理解,更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ego(自我),我不能理解“我”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因而不能平静处理问题。我教训他,斥责他,然后我们会争吵,而且越争吵,Quentin和我的愤怒都会越升级。有时我也会说些,“如果你这样的话,将来你会……”的话。Quentin虽天性不易想到别人的感觉,却对自我感情异常敏感。针对我严厉的批评,他内心压力很大,但表现出来却是当时我更不理解的更恶劣的行为。观察特教人员与他的交往,也通过他对我的不断指责和我的不断自省,我渐渐理解了他发育的不平衡,接受了“我”的孩子有问题这样一个事实;而这种接受,使我能比较冷静、不带指责情绪跟Quentin对话,因为哪怕你语气中有任何判断、指责他的成分,Quentin都能听出来、嗅出来,知道你的不宽容和居高临下,也使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追问或教导他,更让我学会了以真诚的正面表扬来鼓励他。而这些态度和习惯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中,使得周围的人们都更愿意和我合作、交往。
英文里有个说法,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Quentin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美国幼儿园至12年级的公立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每个公校系统的经费,大多来自其所在镇或市各自征收的房地产税。学校花在Quentin身上的人力、时间和财力,远远超出一个正常孩子的水平,这意味着全镇纳税家庭都在资助他的教育。事实上,我们镇因为特殊教育很好,吸引了很多有自闭症、ADHD、学习障碍等孩子的家庭。而镇上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文化,不但欢迎这些家庭,而且每次当地教育委员会选举时,所有候选人都有继续镇上慷慨资助特殊教育的共识(镇上目前28%的教育经费用于特教)。学校老师和校长们,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中,的确以服务学生和家庭为宗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我以前对公立学校在两方面持有怀疑态度,一是其是否能同时提供良好的普通和特殊教育,二是对于特教孩子,其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等和高质量教育”。对于前者,我想最好的解答是这样一个事实:镇上高中学生成绩,在麻省300多个城镇学校里,排名总在第10左右。对于后者,Quentin在镇上的经历,打消了我的疑虑,同时我还了解到,为了能够满足各种有障碍孩子的需要,我们周围几个镇各自开发自己的特教专长,以便共享并节省资源。比如,Quentin哥哥的一个同学有焦虑症。因为我们镇上满足不了他的教育需要,学校系统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到一个有为焦虑症孩子开设小班的别的镇里的公校去上学。正是这些经历,使我成了公共教育的坚定支持者。学校之外,我们还得到了来自邻居和社区的各种帮助。如此受益于社会和社区体制以及众人的帮助,是一个让人非常谦卑和感恩的经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让我对弱势群体有了深刻的同理心和爱心,使得我在政治上更倾向于自由派立场和给弱势群体赋能的公共政策。
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nature(天性)对nurture(培育)的问题。Quentin 过去一两年里的成长,在多大程度上分别归功于nature和nurture,是我或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最困难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多年来家庭、学校和医生的nurture,似乎总也敌不过nature。大自然让人敬畏。记得在一本探讨精神健康的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One began by finding mental illness mystifying, and ended by still more mystified by health——你开始时觉得精神疾病很神秘,最终却发现精神的健全更为神秘”。造人造物的过程,似乎太容易出错了,而任何纳米层次的错误,都可能导致疾病和障碍。所以我们大多数人生来就有健全的身体和精神,的确是大自然母亲在上演一次次的奇迹。但在敬畏大自然的同时,我对周围帮助过我们的专业人员、对特教系统的不懈nurture努力,产生了无比的崇敬。
Quentin和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艰巨。Quentin如何度过青春期、最终能否自立、如何应对由于与人交往障碍所导致的孤独与抑郁等,都是我们不能不担心的问题,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像过去这么多年里周围支持我们的人们所表现的一样,保持希望并孜孜矻矻地努力。■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