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我从平和步入哥大!英美文学带给我的审美享受和存在性焦虑…
#1
写在前面
读者您好。
现在您眼前所见的这些文字,是我第三次新建空白文档,写下的第三个开头。
在这样矛盾心理的作用下,我的前两稿文章不尽人意:风格混杂,内容过多,在叙述和论证之间摇摆不定,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来回跳跃。这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中,大臣Polonius给Hamlet介绍宫廷来访剧团的一段台词(来自剧本的第二幕,第二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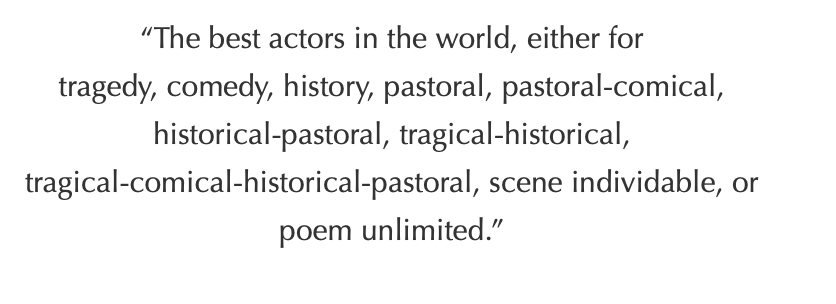
我的文章似乎也变成了一个tragical-comical-historical-pastoral(“历史田园悲喜剧”)的“四不像”。
因此,在进行了取舍后,我决定聚焦于英美文学——我将要在大学攻读的专业——在最近几年给我带来的诸多反思、感悟和改变。这篇文章不是关于“专业探索”,也不是关于“热爱如何帮助我申请上好学校”。我只想谈谈,作为一个母语为中文的读者,阅读英语文学、走进西方经典的私人体验,跟大家说说心里话。让学弟学妹们了解学习的终点不是申请,而找到热爱——你愿意为之持续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东西——让自己时常有一种overwhelming的快乐和坚定的内心。这时,校内成绩/标化考试/申请/亲子关系,一切你所烦恼焦躁的事情都变得不那么难以面对了。
#2
英美文学带给我的审美享受
“文学有什么用?”
每当身边的人知道了我的专业方向,随后向我问出这个问题时(相信我,我被问到过很多次),他们总是会使用一种礼貌的语气——声音里夹杂一种纯粹的好奇,一丝略带歉意的无知——像是生怕冒犯到我;而我总是会用一句“嗯,这是个非常深奥的问题”来敷衍了事,略带幽默地结束话题。
提问者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意图,而很大一部分,在我看来,实际上问的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学文学专业的学生,将来能做什么职业?有前途吗?”不同于商科、经济、计算机科学,文学似乎无法匹配到一个单一的、在当今社会能有所谓“很好发展”的职业领域,因此“没用”二字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是个非常自然的、直觉性的反应。
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有一个精心打磨、屡试不爽的答案:“哈哈!事实上,English专业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比如新闻工作、电影/戏剧工作等等,并不是所有毕业生都成为了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很乐意将来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把我对语言文字和经典文学的热爱传播给更多人。更何况,还有很多时间去给我尝试呢!”
这些都是实话,且能满足大部分提问者。但我知道,这并没有解答“文学有什么用?”的根本问题,只不过解决了“学文学之后能干什么”。从幼儿园时期阅读儿童漫画,一直到如今阅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作为一辈子的读者,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我的困惑。因为很长时间以来,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阅读文学作品当然是为了学习——学习书中的“道理”,书中的“智慧”,本质上和数学课学习三角形的运算,生物课学习DNA结构没有区别。从小学到初中,当每篇课文,每个文本都能轻而易举地被提炼出“中心思想”,一个应当在考试中被写进答卷的标准答案,你很难不去认为,阅读文学作品就是为了寻找这些“思想”。
然而,随着我近几年接触到更多西方文学经典,为自己的英美文学学习作准备,我发现提炼“思想”或“道理”成为了越发困难的一件事。倘若你问我,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教会了我什么道理,我会哑口无言,瞬间语塞。我或许会回答你,它们所涉及到的主题(艺术、战争、爱、历史、文化),或是作者可能在进行的一些讨论(比如《科利奥兰纳斯》对罗马共和国政体的反思),但我无法告诉你它们的“道理”;或者说,我不愿去做这样武断的归纳。从这些庞大、复杂、丰富的文本中“提取”出一条明确的有关价值判断的论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或是作者在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并非不可能或完全没有价值,但这样的归纳往往会抹去伟大艺术作品中常有的模糊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回想起初中语文课本对《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总结(“歌颂仁爱、友谊和爱情,塑造了夏洛克这一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我总会无奈地叹一口气。夏洛克作为一个复杂多面、有血有肉,值得同情的个体,在这样简单总结出的“中心思想”里荡然无存。而《威尼斯商人》作为莎士比亚“问题剧”(problem play)的内在矛盾和复杂点,全都被忽视了。
《威尼斯商人》里的反犹主义呢?这部剧本身是反犹的,还是说只是探讨了反犹的社会现象?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观众会如何对夏洛克这个人物做出反应?《商人》如何回应了克里斯托弗·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莎士比亚自己有种族偏见吗?在解读他的作品时,莎士比亚的私人立场真的重要吗?我不认为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任何人能为这部莎剧总结“道理”。所以,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文学学习中,提出问题或许比寻找答案更有价值。
但就我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些“道理”似乎不是我作为读者在文学作品里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很明确自己喜欢《哈姆雷特》或《白鲸记》(Moby-Dick)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教会”了我什么。我不以作者为老师,更不以作者笔下的人物为榜样。
回想我所读过的经典作品中,最震撼到我那些人物:乔叟《坎特贝雷故事集》中的巴斯夫人(The Wife of Bath)、荷马《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Odysseus)、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Satan)、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Leopold Bloom)、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斯万(Charles Swann),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麦克白(Macbeth)、理查二世(Richard II)、《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Falstaff)——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榜样(我可不愿变得像哈姆雷特那么忧郁,像理查二世那么傲娇,像福斯塔夫那么...胖?)。
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在美学层面上崇拜他们、在感情层面上同情他们、在理性层面上分析他们、在私人层面上了解他们——甚至超过现实生活中我对朋友们的了解(每一个读过《尤利西斯》的读者,肯定比了解自己的好朋友更了解布鲁姆)。通过阅读,我在和这些鲜活、立体的人物进行对话、建立关系,而这个对话本身带给我的就是一种内在自我的扩大和成长。我不需要从中学到什么。这个过程不属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评判体系,因此也无关“有用”或“无用”。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那我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些作品呢?不是因为它们有道理有智慧,不是因为它们是榜样,也不是因为它们有用。奥斯卡·王尔德在给一位名为Bernulf Clegg的牛津大学学生的书信中曾写到这么一段话——在很大程度上契合我自己对阅读的理解:
“Art is useless because its aim is simply to create a mood. It is not meant to instruct or influence action in any way. It is superbly sterile, and the note of its pleasure is sterility.”
王尔德,以及他所强烈支持的唯美主义思想(aestheticism),提倡“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是完全非功利的,它的内在价值不在于它的社会或政治属性。艺术不能帮助我们改变生活,不能“教我们做事”,更不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它的价值仅仅就是“创造一种氛围”罢了。
尽管我不认同非常极端的唯美主义——文学终究无法脱离历史、社会和政治,文学也蕴含着反映社会与政治的能力——但作为读者,我喜欢这些书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纯粹的美学价值,也就是王尔德所说的“氛围”或情绪的营造。文学不就是(以一种其他艺术形式都做不到的方式)去捕捉情感,随后将其转化为语言文字,从而分享给所有人吗?而我们,作为读者,不就是去调动自己的感官,去体验这些情绪吗?理性的分析当然是必要的,但乐趣的最大来源是感性的体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小说《微暗的火》(Pale Fire)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深得我心:
“The subject of teaching Shakespeare at college level having been introduced: "First of all, dismiss ideas,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train the freshman to shiver, to get drunk on the poetry of Hamlet or Lear, to read with his spine and not with his skull." Kinbote: "You appreciate particularly the purple passages?" Shade: "Yes, my dear Charles, I roll upon them as a grateful mongrel on a spot of turf fouled by a Great Dane.”
怎么学莎士比亚?把别的都忘了,首先“get drunk on the poetry of Hamlet or Lear”——让莎翁把你灌醉了再说。先用你的脊椎去“读”,再用你的大脑去读。的确如此!当代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来自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教授,作为王尔德的坚决拥护者,同样强调“美学价值”(aesthetic merit)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提倡文学阅读回归最纯粹的美学体验。在美国学术界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政治因素在越来越频繁地影响着文学学习与研究。布鲁姆教授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视作一个即将消亡的传统的捍卫者,打着一场似乎终将失败的战役。但是,正如布鲁姆教授在许多采访中所说,就算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从个人读者的层面来看,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美学欣赏是不会消失的。
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布鲁姆是这么阐释文学阅读的意义的:
“The true use of Shakespeare or of Cervantes, of Homer or of Dante, of Chaucer or of Rabelais, is to augment one's own growing inner self. Reading deeply in the Canon will not make one a better or a worse person, a more useful or more harmful citizen. The mind's dialogue with itself is not primarily a social reality. All that the Western Canon can bring one is the proper use of one's own solitude, that solitude whose final form is one's confrontation with one's own mortality.”
我不同意布鲁姆教授的许多观点,但他提醒了我要去成为怎样的读者,也提醒了我阅读伟大文学作品的本质:这是一个调动所有感官去体验其他世界的过程,一个代入所有情绪去认识其他人的过程,一个投入所有注意力去捕捉某种氛围的过程,一个扩大内在自我的过程,一个私人享受的过程(“The mind’s dialogue with itself is not primarily a social reality”)。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学习历史,了解哲思,审视社会,洞察人性。
但最终的最终,学到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阅读时带来的“difficult pleasure”本身。多次,当我在阅读莎士比亚、普鲁斯特、纳博科夫等作家的文字时,我会突然从椅子上蹦起来,激动地指着几行字,兴奋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在这些时候,我会感觉自己短暂地触碰到了所谓的“崇高”,体验到了最纯粹的美学意义上的快感。这是一种仿佛心脏上压了巨石,近乎窒息的感觉。这是一种仿佛千万只蝴蝶同时展翅,在脑海中如烟花般绽放的感觉。也正是在这些时候,一切关于有用和有害,关于“道理”和“智慧”的考虑转瞬即逝,我只想延续这种快乐——这种在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中我都从未发掘的快乐——并永远沉浸于其中。
这种感觉,就像是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小说《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主人公Alex躺在床上,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感觉。伯吉斯继承乔伊斯的笔法,用疯狂的语言创新和娴熟的通感手法描述了聆听音乐时的全身心享受:
“Oh it was gorgeousness and gorgeosity made flesh. The trombones crunched redgold under my bed, and behind my gulliver the trumpets three-wise silverflamed, and there by the door the timps rolling through my guts and out again crunched like candy thunder. Oh, it was wonder of wonders. And then, a bird of like rarest spun heavenmetal, or like silvery wine flowing in a spaceship, gravity all nonsense now, came the violin solo above all the other strings, and those strings were like a cage of silk round my bed. Then flute and oboe bored, like worms of like platinum, into the thick thick toffee gold and silver. I was in such bliss, my brothers.”
或许有点“meta”的是,我在读这段文字时,我也感受到了“wonder of wonders”;穿透Alex灵魂的是贝多芬的音乐,蔓延我全身上下每个细胞的是伯吉斯完美的prose。
#3
与时间对抗
英美文学带给我的不全是享受,还有一种折磨人的、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
我从小学开始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初中七、八年级开始接触莎士比亚——英文阅读对我来说一直是很平常、很有乐趣的一件事。但在十年级确定以英语为申请专业后,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恐慌和紧迫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读过的英文原著还太少、自己的英文语言能力也不够好(对于读文字上有难度的文学作品来说),以及将要和自己竞争的大多是英文为母语的文学爱好者们。毕竟,中国留学生群体内,有多少人申请这个专业呢?
这种恐慌感转化成了一种对于时间的强烈感知,似乎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源自于“时间太少”。的确,在高中繁忙的学业压力下,每天挤出时间静心阅读,似乎是格外困难的一件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快节奏时代,太多事物——社交媒体、短视频、游戏——可以提供即时满足感,时时刻刻争夺着人们的注意力。有一次有朋友问我:“怎么才能做到长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书上,克制住自己不看手机?”我回答:“这是做不到的。”唯有把手机关机,放在另一个房间里,确保自己接触不到,才能维持较长的“无屏幕时间”。这是当下人类的“通病”,和自控力无关。最近我看了《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新文章,标题是“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英语专业的终结,非常震撼人心的标题哈!)。
这篇文章的作者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世界顶尖的莎士比亚学者James Shapiro(在几个月前,我也有幸和Shapiro教授通过邮件交流了关于莎剧《科利奥兰纳斯》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校内见了);Shapiro教授表示,自己在20年之前能够一个月读五本小说,如今一个月能读一本已经算很多了,因为太多时间都花在了网站、视频、播客上。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文章中提到,让学生阅读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简直难如登天——我自己也没能读完Middlemarch,在差不多第两百页的位置放弃了。
但认识到问题的普遍性,并不能消除我的恐慌感。这种“我来不及看这么多书”的阅读焦虑在两个场合下最为明显。
一是在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脑海中回想着自己一天做的事情,尤其是自己一天读的内容,很快就会陷入到“如果我一天读这么多,那一个月能读xx本书,一年能读xx本书,一辈子能读xx本书”的计算中。算出的结果,永远令人失望。这句话可能从一个十八岁,迈向十九岁的人类个体口中说出有些奇怪:但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我很强烈地感觉到时间在从我的身体里流走。
二是在图书馆和书店。在过去的2022年,我最常去的是福州路的外文书店。看到满书架的书,激动和恐慌、兴奋和焦虑,几乎是同时涌上心头。那种想要马上沉浸在书海中的喜悦,总是伴随着“我能读xx本书”的计算。一旦陷入了这个害人的计算过程,我就会意识到自己一辈子能看的量,不过是我眼前的这两个小书架——我视野中的这个小角落。随后,我会把这两三个书架的宽度想象成我人生的宽度。没错,我会失望地对自己说,就这么点。这时,自己的生命无比渺小、无比短暂的残酷事实仿佛写在了眼前每本书的封面上,它们盯着我,嘲笑我。
因此,正是对英美文学的热爱,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生的长度,时间的短暂。从左边书架到右边书架,不过是60年、70年(运气好的话)的一条路。而我正在这条路上飞速行驶。我最近读完了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Speak, Memory),这本书的开头把人生比作“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而这个光明的缝隙和前后两片黑暗比起来,实在太过渺小:
“The cradle rocks above an abyss, and common sense tells us that our existence is but a brief crack of light between two eternities of darkness.”
纳博科夫的用词“a brief crack of light”让人立马回想起《麦克白》中“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的独白,其中莎士比亚把人生比作“brief candle”。这是我最早会背诵的一段莎剧独白,也是我认为书写人生的荒诞、短暂与无意义的最好段落之一: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in thi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The way to dusty death. 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时间与死亡是文学中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我能感同身受的文字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学作品还带给了我一种和“时间焦虑”截然相反的体验:文学帮我意识到了自己所拥有的时间之少,却又给予了我打破这些时间的可能性。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我的精神世界不仅限于当下,而是蔓延于整个人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当我阅读古希腊的戏剧家们,比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我仿佛就生活在雅典;
阅读王尔德和Saki等作家时,我仿佛就生活在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中上层社会;阅读莎士比亚时,我存在于太多地方:古希腊(《仲夏夜之梦》)、古罗马(《尤里乌斯·凯撒》、《科利奥兰纳斯》)、英格兰(每一部莎翁历史剧)、苏格兰(《麦克白》)、丹麦(《哈姆雷特》)、意大利(《罗密欧与朱丽叶》)、西班牙(《爱的徒劳》)。尽管自己的肉体存在是固定于当下这一个空间的,文学让我的精神存在能够穿梭于时空,去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人建立永久的关系,摆脱现实生活中飘忽不定的关系和情感。
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最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去年一段时间里,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情是被痛苦、失望,以及孤独所定义的。困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被海量信息淹没。从信息过载带来的不知所措,到努力挣扎后的身心麻木,离开学校,开始网课头两天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堆积的负面情绪。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帮我打破了自身所处的时空,让我的精神世界可以逃离令人失望的现实世界。
在这三个月里,我阅读了20世纪现代主义最伟大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我读完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半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以及被许多人称作“天书”的小说巨作《尤利西斯》(Ulysses)。在三百多页的导读本(Patrick Hastings老师的Guide to Ulysses)和六百多页的注释本(Don Gifford的Ulysses Annotated)的帮助下,我让自己完全地沉浸于《尤利西斯》的世界中。在去年年终阅读总结的朋友圈中,我写了这么一句:2022年,身在上海,但心从未离开过爱尔兰。
因此,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如何读,为什么读》(How to Read and Why)中的这句非常正确的话:
“We read not only because we cannot know enough people, but because friendship is so vulnerable, so likely to diminish or disappear, overcome by space, time, imperfect sympathies and all the sorrows of familial and passional life.”
不同于现实生活,阅读所建立的“friendship”和“sympathies”是顽强的,是“完美的”,是不会随着时空的转变而减弱的。
简而言之,在与时间的纠葛中,英语文学经典给我的感觉是双重的、矛盾的:这些书既让我感知到了时间的飞逝,又为我暂停时间,品尝永恒。
#4
这里就是我的疆域
最后,我想聊一下本文的标题:“Here is my space”。这四个词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的第一幕,第一场,是古罗马后三头联盟中的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对自己的恋人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所说的。完整的台词如下:
“Let Rome in Tiber melt and the wide arch
Of the ranged empire fall. Here is my space.
Kingdoms are clay. Our dungy earth alike
Feeds beast as man. The nobleness of life
Is to do thus; when such a mutual pair
And such a twain can do ’t, in which I bind,
On pain of punishment, the world to weet
We stand up peerless.”
在英美文学中,从莎士比亚的台词里截取几个字作为自己作品的标题,是最常见、最“老套”的行为之一。最有名的例子有:福克纳的《喧嚣与躁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书名出自《麦克白》);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后现代小说巨作《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出自《哈姆雷特》);当然,还有前文中提及的《微暗的火》(Pale Fire,出自冷门莎剧《雅典的泰门》)。我也来致敬一下这个传统,截取莎翁的这几个词(似乎还没被任何有名的作家用过?),作为本文的标题。当然,这句话不是随机选的。安东尼的这句台词承载了我的一段回忆、一丝自我怀疑,以及一份相应的心理安慰。
首先,说说这个回忆:《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是我在现场看过的第一部莎剧,也算是我对莎士比亚的热爱的起源。2017年暑假,我参加了一个莎士比亚戏剧夏令营,和英国当地的一些初中、高中生一起表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对夏令营课程的补充,老师们当时带我们前往了莎士比亚的故居斯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观看了皇家莎士比亚剧团(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当时上演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
在观看表演前,我并没有读过这部剧(事实上,我当时没有完整地读过任何一部莎剧。我们表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删减版的剧本。回国之后,读了未删减版,才品味到莎翁原汁原味的诙谐),因此在观看过程中,大部分台词都是听不太懂的,只能根据舞台布景、人物动作,以及台词里的关键词,对剧情进行很基本的推断。但也正是在这个“听不太懂”的情况下,我被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
莎翁的语言如海浪般扑打在我身上,充满韵律与魔力。搭配上金碧辉煌的舞台布景(毕竟是埃及艳后的宫殿)和演员们充满力量的台词表演,莎士比亚的每一个词都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哪怕我当时不完全知道它们的含义。也就是在那次表演(以及几天后在伦敦的The Globe Theatre观看的《第十二夜》)之后,我心里栽培一下了一颗热爱莎剧、热爱英语文学的种子。
选这句的第二个原因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心中总有着一丝自我怀疑:总觉得英语文学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领域,没有中国留学生会学这个的。作为非母语者,语言的隔阂消除后,似乎还有一重文化的隔阂。就算事实是我的英文阅读能力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同龄的英文母语者,就算我已经钻研了大多母语者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的经典文本(曾听过一句玩笑话,“经典”的定义就是大部分人都没读过,但都希望自己读过的书),就算在讨论某些学术话题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英语用起来比中文更流利,但内心无法安静下来的一个声音是:我不属于这里——就像安东尼抛弃了罗马,不顾国事,来到埃及寻欢作乐一样。脱离语境,“Here is my space”看上去像是一句庄严的宣告,实际上只是安东尼热恋之中说出的情话罢了。
我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并不妨碍我对另一个语言、另一个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或任何的艺术作品)有着痴迷般的热爱。每次想到这里,我总会举两个例子提醒自己: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英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最有名的那些作品,比如《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都是用英文写的。
然而,他的母语是波兰语,一直到20多岁英文还说不流利。还有本文已提到数次的纳博科夫——他的母语是俄语,但他在文学创作中把英语拆解、重组,像魔术师一样把英语文字玩弄于股掌之间。我并不是说,我这辈子(或任何一辈子)能成为像纳博科夫或康拉德这样的作家。只是说,在非母语中把文学创作和文学学习做到巅峰造极,是完全有可能的。语言不是障碍。没有什么是我应当考虑的障碍。只要我现在喜欢它——就像安东尼喜欢埃及艳后那样——那这里就是我的疆域。
感谢父母从小到大给予我的关爱、鼓励和支持;感谢在我探索自身热爱的道路上遇见的朋友们;感谢每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感谢文学、戏剧,还有艺术本身。是你们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