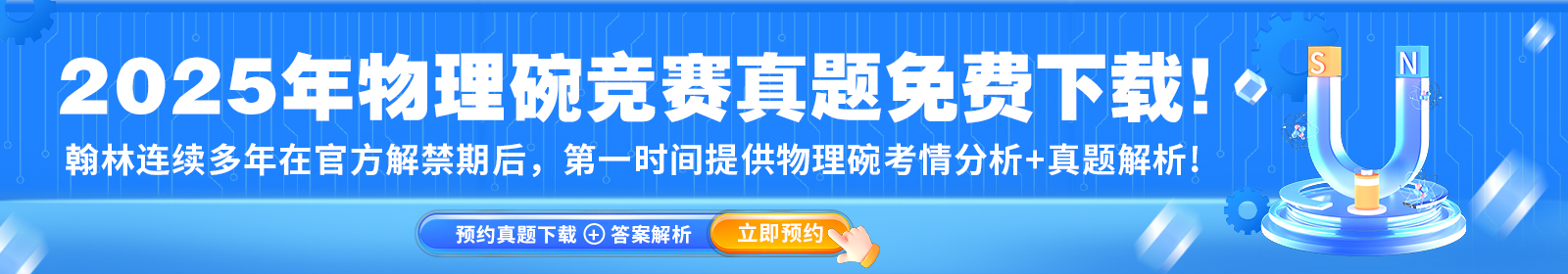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寒门出贵子有多难?美国也没好到哪里去
——《纽约时报书评》
谈到社会阶层的改变,我们今天都将目光聚焦于高考。受到帕特南此书个案式讨论的启发,我也想借此回忆一下自己大约十年前所经历的高考。它是一段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迷茫、挣扎和选择的旅程,然而同时也单纯、朴实、相对简单。记得高二的化学课,我们学校的一位化学名师曾激情昂扬地告诉我们:“高考是千千万万的考生一起,争着过独木桥。”
坐在50多人的闷热的大教室里,我把玩着铅笔,体会着她给我们描述的千千万万人过独木桥的情景,脑海里想到了地铁一号线晚高峰的人民广场,人潮汹涌。正是从这位老师那里,我听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高考是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也是最后一次“公平竞争”;了解到这些后,我们背诵元素周期表就更努力了,做数理化题目也更认真了。
我们不仅会背元素周期表、各式各样的物理公式、化学公式和数学公式,还会用口诀背诵从夏商西周一直到中华民国的中国朝代表,高考那年头脑里想的古今中外、宇宙洪荒的知识,以及对这种知识熟练掌握的程度,或许已经超越了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我记得当时每天放学前,笑眯眯的数学老师都会在黑板上,留下两道难易适中的题目,让我们回去研究;翻看那时留下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公式、符号,以及“数学十六字箴言” — “弄清问题,找准联系,解后反思,增强悟性” — 这是非常好的解题经验,想要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寒门学子,要学会谨慎地在针尖上跳舞,步步为营,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道题目,完成每一份答卷。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学习很多更复杂的事情,例如怎么估算自己的成绩和志愿,怎么写非常八股又显得略有新意的语文作文,怎么在高考那三天保持平静、全神贯注地发挥到自己最好的状态。从高考前三个月,我们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演练,预备着那场即将开始的无声的战争,想象着自己走在千万人行走的独木桥上。有许多人开始暗自准备,有的通过金钱买到独门秘籍,有的偷偷参加补习班。
然而我没有办法阻挡对各种不可预测的可能性的恐惧,害怕不会做数学卷子的最后一道大题目,也讨厌应试作文的写法。考试前三个月,我索性向语文老师提出,我不再参加语文课的训练。当时的自己实在是对这一整套应试教育的做法和实践、对语文考试固定的答题规范、以及高考作文的议论文写法,反感到了极点。我的这一请求换来了语文老师非常惊讶的表情,她告诉我,不要对自己自视甚高;如果要求退出她的语文课训练,我必须提供由我父母签名的报告,我自己的报告,这些最后都要经过校长签名,才能生效。
高考的时候,面对当时的作文题目,我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犹豫。我很想写在考场外徘徊等待的家长们,写我自己的父亲,写高考那天早晨唤我起床的母亲(高三的时候,她经常陪我读书,一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早晨六点又起来帮我准备早餐),我想写我眼中的他们。这场考试被赋予了太沉重的意义。父母的期盼,朋友的支持,老师的培养,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最后三天你所获得的一个分数。然而握着黑色的水笔的十八岁的我犹豫了,那个时刻,我想起了语文老师提供的周全的应试策略,想起她说最万无一失的做法是写一篇四平八稳的议论文,这样无论如何不会出错。
高考与美国梦的相似之处
我所叙述的高考经历,表面上似乎与帕特南所讨论的“美国梦” — 那种机会平等、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从而实现向上流动的机遇 — 非常相似,即便要和千军万马争夺独木桥,但理论上寒门子弟依旧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梦想的。
高考是一场残酷的竞争,许多孩子失败了,也有一些孩子,顺利地通过高考走到了更高的平台。我那时候遇到的大多数同学,都生长在最普通的家庭里;我们的父母,许多都是这个社会里最最平凡的普通人,靠着微薄的薪水,省吃俭用,付出了他们的全部心血,爱惜并供应着我们的成长。
进入大学以后,我遇到了许多不怎么学习的韩国同学,轻轻松松就能考进来的港澳台地区的同学,低调而神秘的、出身优渥的同学,通过各类特殊渠道加分有特长的同学。他们许多人都在本科阶段去世界各地交换学习;那时我们宿舍的信箱里因此也经常收到各种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明信片。一位会唱歌剧的女同学,一会儿在西班牙,一会儿在古巴;一个马来西亚籍的留学生,从巴黎给我写信,要我快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香港的同学去旧金山看姑妈;北京的同学暑假去了伦敦,明年夏天打算花好几万去耶鲁参加暑期学校……
在考试中的逆袭的“学霸”们,后来怎么样了?
寒门出身的同学并不多见,每个班级大概只有那么几个。大多数人都比较低调,田田是一个例外。我的一个朋友田田,来自农村,她从不隐藏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乐于与我们分享她的成长故事 — 她的家庭非常贫困,然而她也异常懂事,从初中开始就不拿家里一分钱 — 遇到她,是一个欣喜的意外,她的许多故事,都使我大开眼界。
她节省,努力,有时在这里打工,有时在那里兼职,在二十岁的年纪品尝了许多本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的心酸。也就是她,执着地在大四的时候申请美国的高校,并且拿到了哈佛大学某个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然而最终她不得不放弃,因为没有办法筹到足够的钱,支持她前往美国念书。作为她的朋友,我见证了她所有的拼搏,以及拼搏到最后不得不做出的妥协、让步和放弃。
这之后,她曾经带着很少的钱,跟团来过一次上海。我带她逛南京路,带她吃小笼包,又很担心她身上钱不够花。临别的时候,望着外滩,她告诉我,这不是她的城市,而只是我的城市。她的神情是迷茫的。她非常优秀,充满热情。她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女孩子。
然而她独自面对了许多失落的时刻。现在她仍旧在一个人默默打拼,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里,坚强地奋斗着,从来没有放弃过。当年考上大学,她的故事上了当地某报刊的新闻头版,一时轰动周围。仿佛从那一刻起,人生就改变了,并且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光辉的时刻。然而新闻并没有持续地报道她的故事。
我们的社会依旧不断去塑造这样粗糙而苍白的“学霸”故事,却没能追踪做继续的报道。
今天有多少清华北大的学生仍旧是出身寒门?这些寒门出身的优秀的年轻人在读书期间,能否像那些出身优渥的孩子一样负担得起去欧洲和美国交换一个学期的费用,他们毕业以后,又能否负担在北上广买房和生活的费用,生存、继而寻找到自己的生活?
更严峻的问题是,这些从寒门进入一流学府的学子,最后是否还能回到自己的贫贱之家,还是走得离家越来越远?他们又将在哪个阶层寻找伴侣,选择在何地安身立命,他们的下一代,是否将站在更高的平台上享受更丰富的资源?《我们的孩子》被译介到了中国,使我更加期待对中国孩子的严肃追踪式研究可以问世。
出生底层的中美年轻人,都要面对的困境
美国出身底层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尴尬当然并不少于我们。我的一位墨西哥裔的朋友,曾向我吐露她的经历。她的父母是墨西哥裔的非法移民。从小她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与父亲离异以后,带着她四处奔走,有好几年时间都只是在一辆破车上生活,无家可归。她通过努力,进入美国不错的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并且成绩优异。
现在她是常青藤拿全额奖学金的博士生,喜欢逛街,对纽约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了如指掌。然而她毕竟没有办法像大多数常青藤学校的孩子一样自信、无忧无虑。她曾经向我们坦言,她的亲戚们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回到他们身边,她往往不知道同他们谈些什么;儿时所遭遇的父母离异的经历,也显然在她心头留下阴影,她时常担心遇到靠不住的“渣男”。
她的经历很像是帕特南在书中分析的许多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自小生活在不安定、支离破碎的家庭里,有的在没有父亲陪伴的“组合家庭”(blended families)里长大。伴随他们成长的不是其乐融融、充满欢声笑语的大家庭,而是发脾气的、酗酒的父母,贫穷且吸食大麻和海洛因的邻居,是居无定所、漂泊流离的生活。
帕特南指出,这些出身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要经历更多坎坷,才能获取同龄人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是因为底层的父母往往限于阶层和视野的局限,无法让孩子接触优质的社会资源,有时也没有能力支持孩子念大学。此外,学校的诸多安排,也在扩大社会阶层的差距(第206页)。
这一点与中国的社会十分相似。在教育条件相对落后的乡镇,师资资源缺乏,而在师资资源相对集中的大城市,获得“名师”的指导往往需要通过参加课外补习班。贫富差距非常明显,寒门出身的孩子往往很少有机会在高考以前遇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辈或者长辈,然而这些对中产阶级的孩子而言并非难事。
本科时代与一些同学一起走访地方时,我们获得了当地政府和领导的宴请,当时有一位家长立即就打电话请来自己即将准备高考的女儿。记得那晚我们纷纷向那个幸运的女孩子分享了自己高考的经历,还留了联络方式,在高考的时候给她进一步鼓励;而这样的经历,对寒门出身的孩子而言,根本是天方夜谭。
当然,我在这里集中讨论了高考作为改变莘莘学子所属社会阶层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然而众所周知,许多看似不那么关键的考试,却扮演着事实上也很关键的分化的角色。小学升初中就是一次关键性的分流,小孩子进入怎样的中学决定了能否在最具备可塑性的年龄段尽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除此之外,在大学阶段选择何种专业,毕业以后是出国留学、在国内读研究生还是参加工作、去哪里工作、选择哪一行业,这些选择都将在毕业以后塑造着我们的自我认同以及我们所属的社会阶层。
来自 Consumer Affairs
美国也是相似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在美国是随处可见的、非常直观的现实。教育资源的分配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
纽约中央公园周围立着许多漂亮的高楼,俯瞰哈德逊河和中央公园四季的风景,住在这些街区的孩子像天使一样在街上奔跑,而往 Harlem 和 Bronx 走走,人口的贫困化程度就会马上展现,你会看到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许多一贫如洗,被视为潜在的罪犯;你会遇到戴着棒球帽一起活动的黑人少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帕特南在书中调查到的年轻人一样,“粗俗无礼,满口谎话,无证驾驶,还抽大麻”;费城、芝加哥、华盛顿都有这样触目惊心贫困的街区,而且贫穷往往与特定的族裔(尤其是非裔、拉丁裔)联系在一起。
我曾遇到一个可爱的黑人男孩,年纪很小,不肯好好念书,但他却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地同我说:“你不知道,生活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一点也不简单。”样子非常好笑,但背后的事实也很残酷。种族的差异在民权运动以后看似被淡化了,然而保守主义的回流一直存在,尤其在今天的美国表现尤为明显。
在《我们的孩子》中,出生非裔底层家庭的谢丽尔告诉我们,她从未感到自己真正属于她所在的班级集体,也无法真正融入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种族主义随处可见(第20页)。
中美社会不尽相同的沉重
这一点中国社会当然要友好得多。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里,即便有社会阶层、地域、户籍各个方面的歧视,但至少不会因为自己的肤色遭遇歧视。当然,或许我们会住在四人间的宿舍,而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拥有外国国籍的同学,则很可能住在带有卫浴和厨房的单人间,并且拿着奖学金,这些现实有时也会引发年轻人的思考。
然而在中国的高校里,我们处在一种完全被保护起来的状态,吃食堂、上自习,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由种族和肤色产生的歧视似乎非常遥远。这当然也是一种幸福。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几天,我听一个十八九岁的亚裔女生发表演讲,说她已经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她是 LGBTQ 、是亚裔,父母是非法移民,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她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还会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听懂了她在这个公开场合所试图表达的绝望的意思。我当时极为吃惊,一个才十八九岁、那么优秀的年轻人,居然在这个年纪,就开始面对生活中那么沉重的东西;而这种沉重,与田田面对的却又不同。
十八九岁的我们,生活大多数单纯得好像一张白纸,考试是实现自己成功的捷径,走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或者任何一座 985 或 211 的高校,我们似乎就为父母和学校提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我们不大需要考虑读书以外的事情,家长帮我们操心所有的一切。我们许多人是在念大学的时候才学会自己洗衣服、套被罩、挂蚊帐,并且觉得会这些就意味着独立了;一直到念本科,家长偶尔还会收到学校的备忘录,由辅导员写一封信,向远在另一座城市的他们汇报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一些不放心孩子的母亲,还要跟到学校,住在女儿的宿舍里给她洗衣服、叠被子,同物理课上的助教交流孩子的考试成绩……
在我们这些生活在梦里的年轻人纠结数理化公式和答题套路的时候,美国处在社会下层的年轻人很可能已经不得不开始面对由性、毒品和酒精构建起来的“焦虑、孤独、毫无希望的生活”(第33页)
非裔、拉丁裔、亚裔的年轻人,更必须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准备好应对随时可能遭遇的公开的或是隐性的歧视。对帕特南而言,阶层的差异已经真正创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如果问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了什么”,帕特南写道,“那就是:在今日之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不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第305页)
帕特南悲观地指出,由于家庭和其他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美国梦曾经给予人们的关于机会平等的期望也正在逐步瓦解。
帕特南指出的这些问题深刻而又严峻,不过他所研究的个案样本也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几乎没有谈及在美国人口越来越多的拉丁裔和亚裔所面临的困境。
我刚才举例谈了一个拉丁裔底层出生的女孩子;亚裔的孩子中,不少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的孩子,我也遇到许多。作为亚裔,不论你念书再刻苦、表现再优秀,你总要做好比同龄人更优秀的准备。如果每天坐地铁,“滚回中国”或者“ Chink ”这类侮辱性的字眼,遇到了也不要大惊小怪。就在前不久,网上还流传着亚裔美国人群体回应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歧视的抗议视频,而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本科留学生宿舍的汉语拼音名签,还被对中国有恶意的人集体撕掉。
我的一位学业十分优秀的朋友告诉我,从她自小生活的曼哈顿华埠的底层社群,走到常青藤学校的精英社区,中间要经历很多的曲折,要走很长的路,而即便她已经获得耶鲁、普林斯顿等数个名校有全额奖学金的录取通知书,她都要时刻预备着比身边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同学更勤奋、表现得更加优秀,这种压力始终存在,底层要突破自己原来所属的阶层,走到新的平台,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