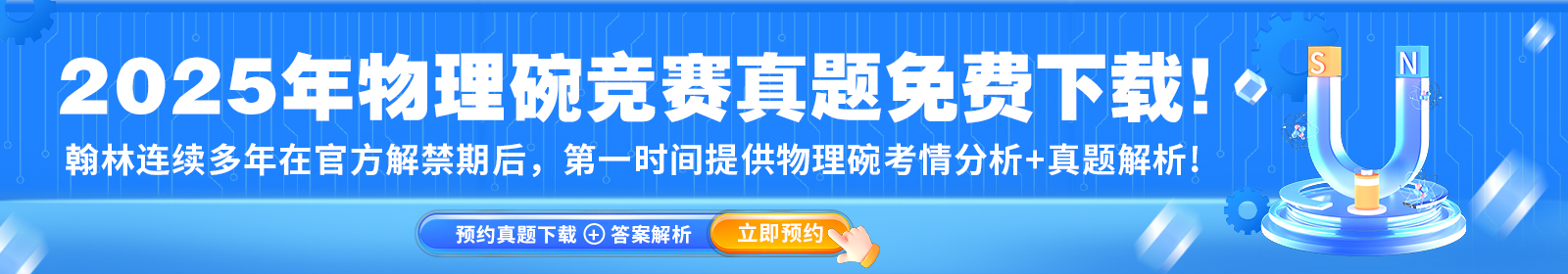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数学竞赛有何意义?从中国两年未获IMO第一说起
在刚刚过去的2015和2016年,IMO(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术活动)总分第一被美国队取得。
中国连续两年未获IMO第一,这是从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从一个没有很强数学学术活动传统的中学里出来,和很多人比起来,我对数学学术活动的了解并不算非常深。
进入大学之后的近20年,我对数学学术活动也基本只是一名旁观者。
我唯一一次参加全国级别的数学学术活动是在1999年,作为入选冬令营的四川队最后一名通过冬令营考试,幸运地被选进入了国家集训队。
那一年我在为进入冬令营的准备中认识了朱歆文,然后在冬令营四川队中认识了张伟,之后又在集训队里认识了陈大卫、刘若川和恽之玮。
我之后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数学研究路上的挚友。
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中,有不少人也从参与数学学术活动开始,成长为优秀的数学家。
一个不完全的名单里包括了安金鹏、何旭华、倪亿、于品、袁新意、肖梁、余君等。
其中的一些人在今天的国际数学界也已经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
这个名单很清楚地说明,数学研究和数学学术活动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怎么解读这个相关性,就是这篇文章的目的。
关于数学学术活动的理解,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参与者自身的经验,一是从作为整个国家教育的一部分。
我将主要从数学研究的角度切入这两个方面。
但是我首先想要强调,尽管我在这里主要讨论数学学术活动为数学研究所作的准备,但这只是数学学术活动的效用之一。
实际上每年参加数学学术活动的佼佼者中,最后从事数学研究的绝对数量并不高。
很多人选择了其他工作,并做出了优秀的成绩,而在他们取得成就的各种素质中,数学学术活动培养出来的能力占有一个显著的位置。
一个令我感兴趣的比较是在不同文化下那些没有选择数学研究的人最后所从事的工作:一个未经查证的说法是中国人多选择了金融,而美国人多选择了高科技。
我见过一个比喻把数学学术活动和数学研究比作“百米短跑和马拉松”。
我认为这个比喻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也许数学学术活动和百米短跑确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需要短时间内的爆发力——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数学技巧上的;但是数学研究的成功所依赖的能力却丰富得多。
好的马拉松运动员大致有着相似的能力,但是让人成为好的数学家的能力却可能大相径庭。
戴森著名的关于“青蛙和鸟”的划分在数学里一般被视为关于问题解决者(青蛙)和理论构建者(鸟)的区别。
单从解决问题的思维类型上而言,既有那种能迅速进入问题,并靠连续不断的爆发力掀翻一个又一个障碍的数学家(科尔莫戈罗夫[Kolmogorov]曾说他考虑解决一个问题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一个星期),也有另外一种数学家,他们擅长一点点深入,持续不断地在同一个问题上稳定前行(怀尔斯[Wiles]花了7年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所以从这里不难看出,数学学术活动能够培养出的能力类型,只是做数学研究的各种能力类型中的一(小)部分。
我认识的一些优秀数学学术活动参加者,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认识到了数学学术活动的这种局限性,而选择了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为后来成长为杰出数学家奠定了关键的一步。
所以对于那些有兴趣参与数学学术活动的年轻人,一定的训练对于数学研究是有益的,但是过度的训练就往往过犹不及,事倍功半,在能力和心理上阻碍了其他数学能力的发展。
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很清晰地记得,自己正是在1999年的国家集训队一个月的训练里,逐渐开始意识到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获得了数学学术活动能给予我的所有东西,需要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
而我的导师科拉(Kollár)曾经两度取得IMO金牌,但他却是匈牙利IMO队里为数不多的来自于非“特殊数学班”的选手。
我相信这种更加平衡的教育对他日后数学研究上的成功有很大益处。
因此我建议对数学学术活动佼佼者进行更全面的教育,把数学学术活动视为整个科学甚至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我相信这对他们漫长的人生之路而言,是更有益的教育方式。
自然这也对数学学术活动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想如果把数学学术活动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让学生通过数学学术活动的学习,而最终跳出数学学术活动,逐渐理解数学作为人类文化里“自由的艺术”的价值,那么这种教育才不会陷入功利的责难而让自身更有生命力。
关于数学学术活动经常被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其中投入多少社会资源。
如前面所说,培养数学研究人才只是数学学术活动的社会效用之一。
因为只从这个角度切入,尽管这里很多讨论也可以被推广到其他情形,但我也并不试图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
数学学术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模式,最积极的一点是让很多对数学有兴趣的志趣相投的孩子,很早地共同处于一个团体之中,相互影响,产生良性竞争。
而这个模式的形成,也为整个社会选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往往在于充分发展属于每个人的最强能力。
而怎么识别这种能力然后加以培养,无论对每个个体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基本的意义,也是教育的核心主题之一。
在这一点上数学学术活动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在数学学术活动中获得最珍贵的经历,便是通过交流,看清了自己的情况,并且走上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一方面我因为数学学术活动,免试进入了北京大学;另外一方面我也因为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认识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后来和我一起从事数学研究的好友,而丰富了自己。
有时候我甚至想,如果能早一点结识他们,也许我会更早下决心从事数学研究。
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是,2000年以后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当中,IMO奖牌获得者的比例显著增高,14名获奖者当中有至少8名分别代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奖牌。
这一方面同这几十年来数学内各学科影响力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在全世界数学的精英教育中,有一种日渐增强的趋势,即把数学学术活动尤其是IMO作为选拔培养数学家的一个环节。
而2015、2016两年美国IMO队教练罗博深是我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的同学。
他现在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副教授,也是组合数学研究领域的年轻专家。
他参与进美国IMO队,也许标志着美国的数学精英教育界在长期重视著名的普特南大学数学学术活动之外,现在也把他们的目光更进一步聚焦在了IMO这样的中学数学学术活动之上。
我想这对于过去二三十年统治了IMO学术活动的中国队,应该是一个很有益的挑战。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