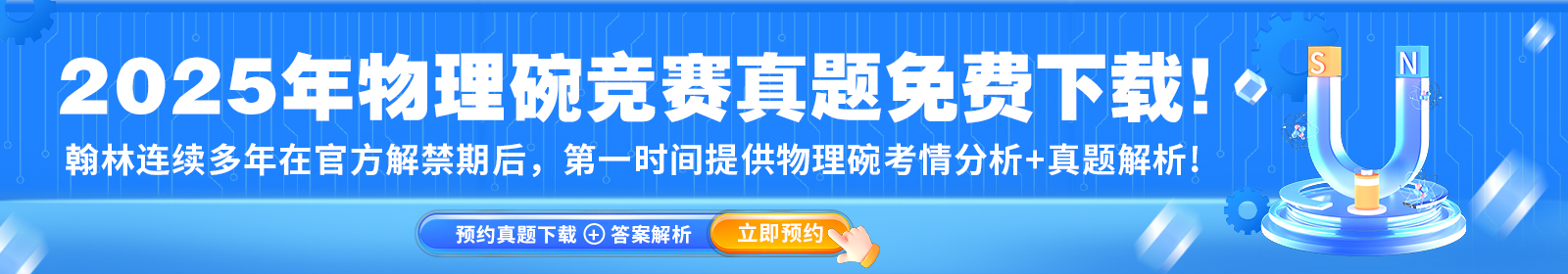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大学的学科分类,美国大学自定,中国“政府主导”?
据媒体报道,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的纪元于2016年3月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了徐州市城建局下属的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一岗位。
随后,纪元的笔试和面试成绩均排名第一。
但在徐州市人社局公布拟招录人员名单前,纪元被告知,因为她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不是招考要求中的“中国语言文学”,所招聘专业和其专业要求不符,因此决定不予录取。
对此纪元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而招考所设置的专业要求中,“中国语言文学”赫然在列。
此外,江苏师范大学也出具了证明,但当地仍未采用。
一、学科分类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虽然对学科概念的具体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东西方对学科的内涵理解还是有着基本共识,例如《辞海》将其解释为:
(1)学术的分类。
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
自然科学部门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部门中的史学、教育学等。
(2)教学的科目。
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而《牛津高级英汉词典》将之定义为“知识的分类;教学科目”。
综上所述,按照某种标准和原则对知识进行分类是“学科”这一词汇的内在本质属性,学科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学术界限的“分类”意味。
诚如Pierce所说的:“虽然大多数研究都不能明确地界定该术语(学科),但它们通常都假设学科的边界与学系(academic department)紧密联系。
虽然这些边界的使用可能看上去是有些把过于具体的限制放置在高度抽象的现象上,从而排除了一大批对此领域感兴趣的人,但是它对创造和维系学科社群的重要性使得学系成为基础,导致学科产生”
但是,学科分类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学者Kockelmans认为,它作为“一簇学习或研究的领域,其特征是一组相互主观的可接受的知识,附属于一个有着很明确界定的实体国度,在方法论准则和程序的帮助下系统地建立在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基础之上”,
所以,学科分类的实质就是不同的“学习或研究的领域”进行利益博弈,“明确界定”其各自“国度”的边界,而最终达成相互“可接受”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为了规范这种博弈行为,避免不同学科的无序竞争和盲目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规则,即所谓的“方法论准则和程序”,而规则的建立,就意味着除了基于学术自身的考量外,学科分类还被纳入到一个以制度化管理的体系之中来。
所以说,学科分类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制度问题。
二、我国政府主导的分类模式
目前,我国较为权威的学科分类标准均为政府部门发布。
如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共设置学科门类5个,一级学科58个,下分若干个二、 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共设置12个学科门类、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在增加了民族医学后达到了382个);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划分了11个学科门类71个大类,计249个专业。
除了政府部门发布的学科分类标准之外,中国几乎没有民间机构从事学科分类,只有极少数科研机构和学者个人提出了零星观点和建议。
例如中国工程院于2004年提出了一个学科分类标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学部专业划分标准》,但主要是“为了便于对院士的学科分布进行分析,加强对院士队伍学科结构建设的指导”,并没有在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且中国工程院本身也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
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方式形成的主要过程是由政府提出,指定各相关部门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制定,再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发布。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明确指出,它是“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由国家科委与技术监督局共同提出,
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负责起草,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国家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司、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司、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干部管理培训中心等单位参加起草”的,
其形成路径是政府推动,“自上而下”,即由政府提出、政府领导、政府参与,通过政府发文、政府组织等方式,在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意见征求及调查研究后进行“编制”并加以“确定”,亦即最终“制定”形成国家标准,体现出浓厚的政府意志。
我国的学科分类对大学具有强大的制约力,分类作为政府管理大学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已成为通用标准并具有法律效力。
在中国,各项由政府资助的课题、基金的申请均是基于学科划分的,必须填写相应的学科分类号,不在目录的研究可能因此而无法申请,同样,不在学科专业目录的人才培养也会因类似的问题而无法授予学位。
因此,大学进行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都必须在政府分类标准的框架内进行。
总之,我国的学科分类标准是要求高校贯彻的指令,是高校进行学科建设乃至办学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三、国外多元化的分类主体
和我国以政府为单一的学科分类主体的方式不同,在西方国家各种比较知名的学科分类标准中,其分类主体高度多元化。
既有以政府为主体的学科分类方式,例如《西德联邦德国政府研究与发展项目分类系统》;也有大量非官方的,由各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乃至以民间机构甚至商业机构为主体自行开发的学科分类方式,
如著名的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编制的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库分类,即基于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和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
引文索引数据库所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计量分析数据库,把人类知识共划分22个学科门类。
这些非官方的学科分类方式和官方的学科分类方式并存,就世界范围而论,它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官方的学科分类方式更为权威,更具有影响力。
美国学科分类的形成过程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
由政府机构从各高校收集现有的学科情况,汇编成目录,供高校学科发展作为参考。
例如,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简称CIP),就是由“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收集高等教育机构名录、课程表等与学科专业相关的各种数据信息,
而后结合自己已有的一些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与其它部门的数据系统,对全国的学科专业进行初步归总与分类,草拟初稿。
随后,国家教育统计中心邀请政府部门、评鉴机构、专业学会和协会、大学管理人员等代表进行研讨,在广泛征求CIP使用者的意见基础上,进行修改并完成定稿”。
可以说每一所大学实际上才是美国学科分类标准的真正制定者,政府起到的作用是对大学已有学科的统计“归类”和适当“处置”,以充分反映现有的大学学科分布情况,同时为高校学科发展提供引导,而不是政府自己单独制定一套标准。
而西方冠以“国家”学科分类的多数办法,对大学无显著强制力,美国尤其如此。
如前所述,美国大学在实际工作中,各有其自己的学科分类方式。
所谓国家的学科分类则是经由政府将各大学的分类归置整理而成的“相对”标准,多作为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学科建设的参考,以起到引导作用,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其实质是“学科目录”而非“学科标准”,具有学术性强和制约力弱的特点,对于大学学科建设更多的是发挥指导作用。
大学仍旧有权按照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采取自己的学科划分方式。
例如排名美国大学前二十位的范德比尔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就可以为每一个学生个体灵活地 学科和专业,并自行授予相应的文凭。
(资料来源:张胤《制度视域下的学科分类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年第5期)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