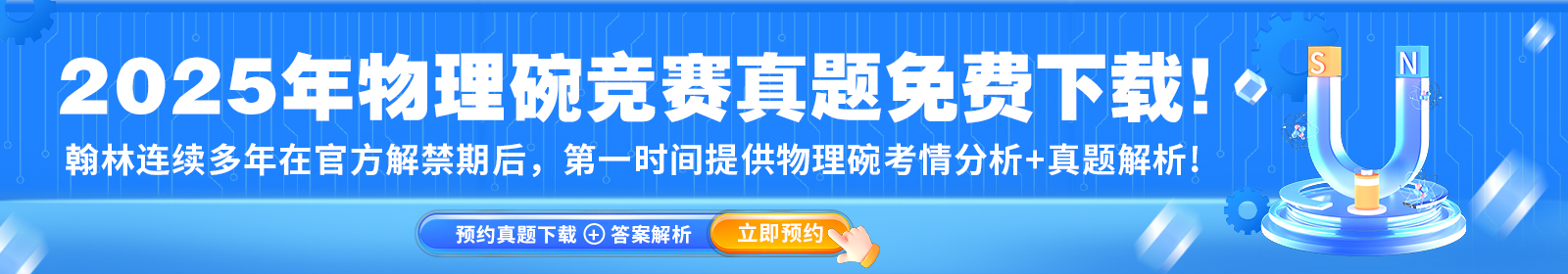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学术反思】斯蒂芬·M·沃尔特:美国高校国际关系专业面临崩坏局面
学人简介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代表作《联盟的起源》等
内容提要
表面上,美国高校的国际关系专业发展有很多的创新点,但实际却积弊深重。
本文将讨论如何对其进行修复优化。
没有人能否认目前是一个学习国际事务类专业的好时代。
社会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各国的竞合深入开展,并与企业、社运、非政府组织、不法之徒和其他许多社会形式产生合作纷争。
曾经毋庸置疑的既有制度和传统观念目前正遭受各种思潮的围攻,几十年来,我们之前所理解的世界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强权政治的回归(在遭遇短暂的停顿与停摆之后),对权力再平衡的思考正在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力每年都变得愈加明显。
全球冲突热度升高,预示着未来几十年将会有更广泛和负面的影响接踵而来。
综合考虑到这一些(还有更多的因素)异彩纷呈的变化,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下有许多年轻人对国际事务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然而,即使美国对国际事务学科建设的捐赠基金在持续增长,美国高校的国关教室里站满了求知若渴的学生,我们这些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学院的教书匠也没有理由沾沾自喜。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是否把工作做到了最好。
我们可能会吸引很多富有灵感的,颇具启蒙意味的学生,并且很快就会为他们之后取得的学术或实务上的成就感到自豪。
但尽管如此,在过去的50年里,国际事务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似乎并不能激励美国不断改善对外政策和获得更好的外交结果。
笔者并不是要将所有的失败归咎于美国各大高校的国际事务学院,但最终,我们进言献策的致用度是否达到了我们的心理预期呢?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曾受到旧有“东方体制”的影响,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以及在创建世界战后秩序方面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人士所展现的那样——
例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等。
然而,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人都没有参加过系统正规的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培训。
比如,凯南拥有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就加入了驻外事务机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的成就却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美国扮演的全球角色日益增多,外交政策的制定似乎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进行支撑。
根据戴斯勒,莱斯里·格尔伯和安东尼·莱克的观点,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层结构正在发生一场巨变。
权力几乎不知不觉地从旧有机构传递给新的美国职业精英——例如从银行家到律师,节省的绩效将有助于培养和管理更多通晓政府事务的人才和全职的对外政策专家。”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对专业知识的重视,将会大大改善派系及“保守势力”带来的弊端,并将产生更明智、更成功的决策。
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由一个更多元化的专家团队来制定,而不仅仅是依赖于一个由商界精英拼凑而成的,具有极强自我选择性的精英群体,他们将接受经济、军事、历史、外交或区域研究方面的专业培训。
从理论上讲,这些见多识广的专业人士之间相互争鸣的观点会引发更激烈的辩论,从而确保对替代性政策的备份和选择被预先进行审查评估,并降低出现重大失误的可能性。
当错误发生时——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受过良好训练和高度专业的政策团体会迅速识别错误并适当采取路线的调整。
本文作者 不幸的是,这种看似纪律严明,引人注目的美国职业种姓形象的确立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界社群的现实情况,尽管在策略,立场和地位上长期求同存异,但伪共识和同质性仍然存在。
专业知识的广泛扩展似乎并不能可靠地转化为更明智和有效地对外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国际事务”的表现行为并不是真正的职业或学术行为,而是政治行为。
有影响力的外交决策人在最初并非要严格按照今后的工作领域选择他们的专业,而选择往往受到意识形态,个人信念,声誉名望,人际关系和政治忠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人们没有被要求必须要通过像美国律师资格考试一样获得资格证书,才能够制定外交政策,就像必须经过专家委员会认证,才能成为心外科医生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在智库机构和政府机构工作的人都在相关领域进行了相当先进的培训,但也有很多人没有任何高级培训的帮助就跻身其中。
想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他颇具影响力的职位资格源自于他的配偶选择,甚至国务卿蒂勒森,拥有的是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是本·罗德斯,一位拥有政治学学士和美术学硕士学位的创意性小说家(诚然这对一个政府演说者来说不是一个好文凭)。
但我们不要忘记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是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问题不在于这些人无能的必然性, 尽管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缺乏严肃的专业训练,但他们都承担或获得了非凡的外交责任与成就。
在美国,至少在国际事务相关学科方面的高级学位可能是很有含金量的,但这不并是参与高层外交政策工作的先决与必要条件。
另一个理由或许更发人深省,高级的专业培训并不能保证完全成功。
外交政策的运行实施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雄心勃勃的大国——哪怕是聪明、勤奋、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都随时有可能会把事情搞砸。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负责外交政策的“火神”队队员们的简历闪闪发光(其中一些人拥有著名的博士学位),但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管理能力基本上是一场灾难。
同样,奥巴马也有很多睿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他工作,但他们却在2009年的阿富汗问题上发出了错误指令,在利比亚和乌克兰问题上也同样遭受了严重挫折。
请注意,笔者并不是在做反智的争辩,也不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官员孤陋寡闻,我们这些学术人士才会有用武之地。
相反,笔者百分之百地确信,在国际事务中,接受过高级培训的人有成千上万,在政府、企业或非营利部门的工作也富有效率。
尽管如此,我们的国际事务类院校仍然可以为这些群体做出更好地学术培训与职业规划。
笔者在美国国际事务类(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度过了18年)院校中经历了一大段美好的时光,以下有五种方法可供参考以提升国际关系学科学习与教学的经验。
1.连接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
众所周知,理论对于政策的分析和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是无限复杂的,我们需要简明扼要的思维因果图来理解事务,确定什么是最为重要的,并帮助我们对预测和决策提供可能性的判估。
没有理论的支撑,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就目前的情况进行臆断,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很少奏效。
此外,对相对糟糕理论(如重商主义、多米诺骨牌理论等)做出高昂代价的承诺,会在决策落地后产生严重的问题。
决策者们有时会嘲笑我们是“象牙塔理论家”,但事实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使用某种坏理论来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而理论的基建对于培养提纲挈领和描绘蓝图的能力则是无价的。
不幸的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没有一个现有的理论是屡试不爽和真正行之有效的——既不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宏观理论,也非联盟,胁迫和制裁这样的中观理论等等,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界各理论派别持有者产生了无休止的争论,并导致了外界人士错误地判定——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毫无价值。
2.讲授一些更为有用的经济学知识。
国际经济学家们非常擅长讲授他们的专业:比较优势理论、国际金融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阅读日益增多的有关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文献等等。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包括笔者在肯尼迪学院的几位同事),他们不擅长讲授国际金融秩序的实质等一系列IPE问题。
(例如SWIFT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老实说,美国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专业类的院校并不善于探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的同事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此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笔者的印象却是,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的经济学课程,美国国际关系专业开设的许多高阶教学课程甚至远没有一些相对低阶的经济学本科专业的课程所学的有意义。
当然,这样的知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如果他们不那么痴迷于“为经济部门的同僚留下好印象”的话,国际事务类学院或许在这方面就能做得更好。
3.历史(尤其是国关史)的学习。
更为严重的教学缺陷是对历史的忽视.在大多数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部门中,外交史和世界史的学习一直以来都处于相对艰难的境况,观察并跟踪美国的国际事务类学院如何能够弥补这一教学不足一直以来是一件有趣的事。
【例如弗兰克·加文(Frank Gavin)最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任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如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的弗雷德·洛文斯(Fred Logevall)、阿恩·韦斯特德(Arne Westad)和莫希克·特姆金(Moshik Temkin)等等】
如果不了解历史进程对国际关系的塑造,那么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国际问题可以被理解,更不用谈如何解决了。
如果不了解乌克兰、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历史,人们怎么可能理解乌克兰危机——并以期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行为有一个客观的解释?
谁又能只知道美伊或巴以的复杂关系,却不知道这些关系背后的历史演变?韩国和日本相处得究竟好不好?....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就不会有任何线索。
这好似程序中一个强大的插件:尽管对现世问题的案例分析或许相似,但对历史叙述的把握程度却会收获截然不同的研究成果。
最后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学生们需要明白,历史不仅仅是名词和时间的集合体,而是一组组相互竞争、相互交织、但仍然截然不同、变化各异的叙述体。
或许在过去,这一学科并没有公开地向我们进行全景式的展示;它是由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和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为我们解释、辩论和建构而成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国际事务专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应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国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过去,因此也没有必要要求看待历史问题要具有绝对的一致性。
国际关系专业人不需要同意别人对历史的看法,但要理解其观点的客观存在性,并且也需要认识到,自身可能需要学会这种以不同视角看待事物的能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洞见。
与“政治正确”或“文化敏感”毫无关系;它能够让人意识到,如果你的目标是说服别人去做你想做的事,那么你就必须知道如何进行着手准备,克服那些在被说服者看来是错误的想法。
简而言之,如果国际事务类专业的学生接受了严肃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后,那么对外交事务的决策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美国各大国际关系专业高校目前可能雇佣了相当数量的历史学家讲授历史,但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课程才是国际关系专业的核心需求之一,这与对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要求是相通的。
像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样,对历史的学术训练是侧重学习如何筛选、衡量和评估材料证据的,这是我们专业在美国国宣时代假新闻横行所需要的必备技能。
真正学习过历史的学生会具有更好的写作能力,避免废话连篇,也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国际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当他们出现研究困惑时,他们会懂得如何去从历史中发掘答案。
这样的训练可能不会创造学术或实务的奇迹,但它对国际关系的学习有百利而无一害。
4.每个人都在谈论“大战略”,但鲜有人去做相关的实证来提升“大战略”。
在美国,也许针对美国政府官员最常见的抱怨就是,他们缺乏一个清晰的战略思路。
笔者自己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撰文指出,而且认为大多数抱怨都是合理的。
但公平地来讲,我们这些讲授国际事务专业的人也没有很好地引导我们的学生进行策略性的思考。
即便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引以为豪的大战略项目课程(该项目也强调历史研究的作用),可能其在培养领导力的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却不能使学生为国家创供清晰连贯的战略思路。
在今天的美国,所谓的“大战略”是十分空洞的,例如前总统乔治·W·布什第二次就职演讲就是一段毫无历史依据的夸夸其谈(“我们应当做X,我们应当做Y,这样我们将成功地保证Z”)
当白宫的工作人员被法律强制要求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他们才聚集在一起拉清单和发布一个响亮的宣言。
以上的努力通常缺乏的是对重要国家利益的明确表述(包括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以及为推进这些利益而制定的具体计划和这些利益可能会引起其他相关参与者的预期反应等等。
战略是连接手段和目的的重要思维方式。
在国际事务中,手段的选择及其部署的合理与否取决于人们对其他相关参与者反应的判断评估。
军事指挥官们喜欢提醒我们,“the enemy gets a vote”,盟友、中立者和其他可能以阻碍或帮助的形式做出反应和介入的人也要统统进行考虑。
一个好的大战略必须是全面的,笔者的意思是,必须要考虑国家在一个问题区域或地区的行动会否影响其在其他区域所推行的对外政策。
换句话说,从战略上进行思考需要一种“全局观”,并清楚地认识到参与者、发展趋势和过程问题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
如果没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世界蓝图——一种能够识别区域重点、各层次行动如何影响世界的能力——那么就很难想象,任何行为体都能在世界舞台上采取有效的行动。
当然,还少不了理论(第1点)和历史经验(第3点)的配套思维。
5.相关的教育孵化基地是否真正合格?也许当今国际事务类学院最大的局限性——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是两党倾向于强化在“自由霸权”和“美国领导力”必要性背后的陈腐共识。
这些机构的院长和教职员都是外交政策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美国的泛权力。
毫不奇怪,这些机构的教师大多由政策取向鲜明的学者和前美国政府官员组成,他们不太可能质疑多年来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与前提。
当然,这种模式有其存在的道理,且有一些明显的优点。
国际事务类学院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对世界问题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当然也对具体的政策问题感兴趣,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渴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同样的描述也适用于在这些机构中任教的大部分教师。
当然,对于学生们来说,向关心现实世界的人以及那些在专业环境中富有经验的人学习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学术机构的发展而言也并不是好事情——问题就在于如何对当代问题进行独立,批判性的研究,并试图分辨有用与无用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把国际关系研究做得更好——
与美国政界发生紧密联系的愿望不可避免地诱导大多数国际事务类院校倾向于聚焦主流的共识而忽视了其他。
可以肯定的是,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有时会出现尖锐的分歧(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对叙利亚进行干预?),但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多年来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正统观点。
不幸的是,美国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院往往是许多国关学生重新审视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唯一场域;这也通常是他们建立智力资本的最后机会,这些智力资本也支撑着他们的生涯规划和事业发展。
因此,国际事务学院应该更多地关注对传统智慧层面的质疑,而不是简单地为现有的国家机器制造训练有素的人力齿轮。
毕竟,独立和广泛的调查研究是一所大学的比较性优势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型捐赠基金是有用的,为什么终身聘任仍然是必要的。
在听完了上述论述后,是否就意味着有抱负的外交政策专家应该避开国际事务专业的研究生学术训练,转而选择法学院或商学院深造呢?绝对不是。
相反,他们应该仔细研究不同的学术项目,找出那些能给他们提供大量智力多样性的项目。
其他的多样性探索也非常重要,包括学生身份背景构成的多样性。
因为人们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通常是可以从周围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就像他们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一样多。
如若想要获得你所需要的基本学术技能——尤其是那些毕业即工作的人——你就应该希望你的先入之见受到他人的挑战与质疑,即使你最终仍然坚持你最初的决定。
但是你却有机会听到不同观点的教授们的言论,然后把握到适合自己的观点。
简而言之,希望在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经历能让学生们成为一个更广博、更有见识、更有自信的思想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简历和技术技能的匠人。
这正是各大国际关系专业院校应该瞄准的发展目标。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