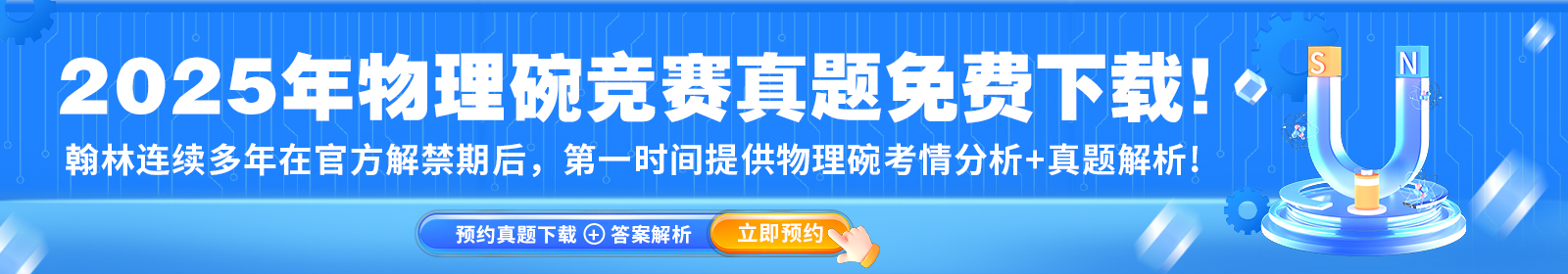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留学生万字长文痛斥父母,决裂背后谁对谁错?
最近,一篇“北大毕业美国留学生的万字长文”刷屏网络。
单从履历看,这位“别人家的孩子”让人艳羡:高考理科状元、北大生物专业毕业、美国TOP50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然而这封长文诉说的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已经有12年没回家过春节了,并在6年前拉黑了父母的所有联系方式,决裂的背后是双方多年以来的矛盾堆积。
通读完这封长文,朕感觉他的人生被分解为了无数个、细碎的至暗时刻。
如果要把这些时刻归类,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控制”。
我最早经历的、但很晚才意识到的危机之一是我家人尤其是我母亲并没有完全接纳我。
她以前多次陶醉地给我讲我两三岁时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并给我看过一张我的裙装照片。
大约我上学前班时,我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着她想像中的女儿“芽芽”说话(我是独生子)。
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在接受红星新闻的采访时,他将化名取为“王猛”,一个刚强无比、充满男子气概的名字。
可在他的少年时代,“刚强”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父母为王猛包办一切,大至选校,小至穿衣,并在必要的时候数落他自主选择的后果。
我五年级时开始在离家四五公里的市里上奥数班,周末我父亲带着我坐车过去,而当时我母亲很不乐意我去。
我当时学起来很有感觉,虽然一开始摸不着节奏,但后来进步相当快。
六年级时一次奥数班考试,我带去的一个很普通的人造革文件夹丢失,找回后发现被人划坏并涂抹。
我回家后我母亲既不痛惜物质损失(确实没必要),也没有用积极的态度安慰我(这一点不妨和下文毕业旅行一起看),而是表现出一种混合了得意和癫狂的怪异情绪,歇斯底里地说:“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了吧。”
王猛一直都是学霸,按理说,优异的成绩本为他增添了选校的资本,但中考结束后,他却在父母的安排下就读单位的子弟学校,他原本心水的是当地的一所名校。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我父母在我读中学的事情上采用了“三步走”策略:粉饰——将中学描述得很理想(但“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的说法足以证明他们自己都不认为二百五十一中水平高。
自己都不信的宣传语,别人自然不会信);否认——在我对学校的恶劣环境已经明确了解的情况下,否认我接触的事实;强迫——表面上承认我反映的事实,逼迫我忍耐中学的恶劣环境并与不喜欢的人交往。
这种控制还延续到了王猛的大学生活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父母为他安排了一位大姨,大姨就像是父母在北京安插的眼线,不断给他打电话,并向他身边的同学了解情况。
到美国后,又推荐了一位“老朋友”照顾他,二人的相处并不愉快,还屡屡发生争执。
有控制,就会有反抗。
也许是长期处于家庭的规训中,王猛的反抗,更像是一种自我损耗。
从小到大,他对父母的安排都是“表面笑嘻嘻,心里妈卖批”,他也曾提出过异议,但在多次“反对无效”后,身心俱疲,最终酿成了决绝的爆发。
在和美国的“老朋友”闹翻之后,王猛曾写过一份4000字的信给父母,详细列出了这位“老朋友”的各种问题,并表示要和她绝交。
可父母却教他“学会跟有问题的人交往”,并称他的信有“狂呼乱叫的味道”。
这让王猛彻底崩溃了。
但让朕哭笑不得的却是这样一段描述:
我预想了他们的四种反应:其一是他们授权我全权处理与姚交往一事,这种情况最顺利,但可能性最小;
其二是他们还可能向我说明,虽然理解我与姚谈不到一块,但他们与姚多年的感情难于割舍,希望我还是尽量与她混个脸熟——那么我坚持不理会姚就行了;
其三,对我最不利的情况,也不外乎是他们难以改变年轻时对姚的良好印象,质疑我讲的事情——即使这样,我想时间也会证明一切(果真如此,只不过这一来就是几年);
最后,他们也可能说“事情重大,我们考虑一下”,然后一拖了之——这也不坏,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直接去忙自己的事就行。
我并没有想到第五种可能:他们把粉饰、袒护二百五十一中学的故事重演一次。
我觉得有基本良心的人都不会这么干——这么想是因为毕竟我还是个学生。
一个成年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为什么要得到父母的授权、甚至还来全权这一说呢?乍看觉得不可思议,但从王猛描述的人生轨迹来看,这并不意外。
长期以来的控制,已经使他的反抗烙上了“请求”的印记,他在沟通的时候不自觉会恳求父母的授权,并把父母的任何拒绝视为下一层的控制。
事实上,此时的他——在美国读心理学的研究生,应该具备独自面对外界的能力,可这种能力一方面在少年时期被剥夺,另一方面,他也在成长后拒绝培养这种能力。
这完全成了恶性循环,你来我往,到了这个份上,撕裂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我知道以我原生家庭为中心的圈子已经变得危机四伏,但我要求生,要争取或有或无的未来,于是摊牌成了唯一选择。
大四除夕二姨挑事后我已经有了决裂的想法,但没能下决心。
经过这几年,姚奉献(美国的“老朋友”)推波助澜,父母执迷不悟,而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成长和觉醒,一切终于无可挽回。
从控制到反抗再到撕裂,令朕触目惊心不是这件事有多么极端,反而是它的普遍性。
王猛的父母就是典型的中国式传统家长,他们条件尚可,说不上多么暴力,但对子女总是忍不住的“关怀”。
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意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应该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塑造自我的人格。
他们总想着带给孩子什么,却没有意识到,从婴儿呱呱落地的那一天开始,身为父母也要从这个小不点身上学习什么。
从生理上讲,成为父母是如此简单,只要你性功能健全。
可就像加拿大作家麦克劳德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自己是爱的衍生,而不只是添置的必需品,都希望在那次勃起之前,是和睦与满足。”
父母应该和孩子一同成长,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以为自己进化到了完全体,但骨子里可能还是个巨婴,于是他们不得不采用老一辈的方法教育儿女,因为经验虽然痛苦,但却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这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矛盾转移,使得自我主体的塑造彻底缺位:我是一个残缺品,时间到了,我要去制造下一个残缺品。
所以很难说王猛在过去那些年中和父母的对话是否称得上“沟通”,因为那完全是单方面的输出和暗地里的较劲,而单就这封长信所呈现的言辞来看,他这个美国TOP50大学毕业的心理学研究生,专业水平是否过硬,也大有商榷的余地。
王猛这种拒绝沟通、封闭自我的状态,原生家庭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他也讲了,自己之所以从生物转向心理学,不就是为了稀释哪些至暗时刻带来的影响,并在今后“平等友善地和娃们沟通与交流”吗?
长信一出,网上有很多声音,在纠结是父母欠孩子一个道歉,还是孩子该同父母和解。
但说实话,意义不大。
道歉无法消解创伤,在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错在哪儿的时候,所谓道歉,更像是临近买单了才端上的菜,让人难以下咽。
而王猛也有不与过去和解的权利,某种程度上,那些疼痛也在倒逼他的成长,虽然那并不愉快。
唯一被忽略的事情是,我们被环境塑造的同时也在改变环境。
当家庭剥夺了自我塑造的机会后,校园是否能在这方面发现问题并给予补偿?王猛所期盼的自我觉醒,是否能在更大的环境中得到启蒙?
可我们具备这样的环境吗?在王猛的万字长文刷屏后,他的父母也终于出面接受了采访,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要说掌控,他17岁以后就不在我们身边,现在34岁了,人生一半都在外边,如果前半程我们在掌控他,可问题出在这后面啊,照这样说,反而是掌控不够。”
这似乎预示了某种规律,宛如酱缸深处。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