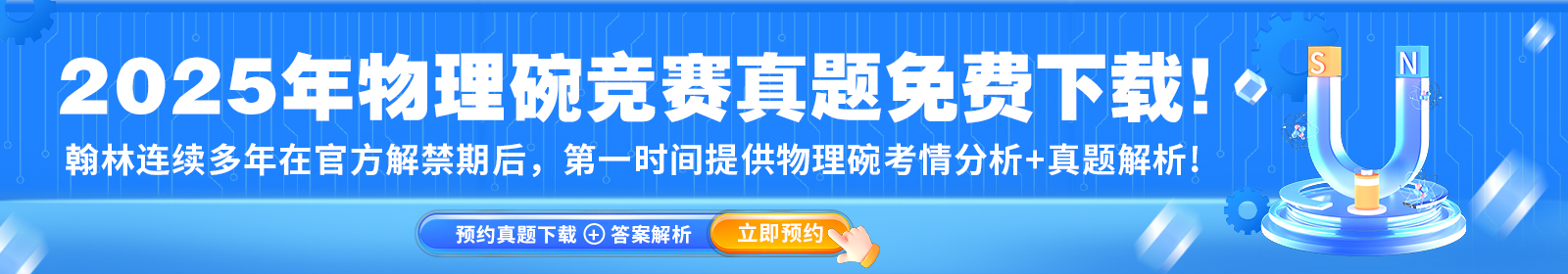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纽约时报筛选出2017年美本申请最出色文书,惊艳招生官的文书长啥样?
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尤其是已经考出比较理想的标化成绩并打算早申的部分同学,文书的准备工作可以在暑期开始启动了,暑期开始准备相对可以减轻下半年正式申请季时的文书工作量及压力。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成功申请美国排名前30大学的学生里面,有60%以上的学生会提前半年,也就是申请年的3月份就开始准备文书的相关工作。显而易见,一篇优秀的文书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出来的,需要不断打磨。 关于文书的具体打磨,弗吉尼亚大学招生官Parke Muth建议:
展示,不要说教(Show, not tell)。因为学生们的文章往往写得很抽象,没有具体细节。所谓具体,即使用那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感受得到的名词以及swim, fly, sink等这些动词。只有当读者能够从文字中读出背后的世界,你的故事才会引人入胜。
《纽约时报》每年征集美国学生关于金钱、职业和社会阶层方面的大学申请陈述,并发表其中最出色的文章。以下是今年的四篇优秀申请书,申请党们可以围观借鉴借鉴,看看“别人家的文书”是如何惊艳名校招生官的。
Tony Lu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索狄尔是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的学生,计划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戴尔和Macbook,我的身份和阶级困境》
马萨诸塞州安多佛
左伊·索狄尔(Zöe Sottile)
最让人兴奋的部分是那台笔记本电脑。
妈妈从我手上夺过厚厚的信封,读出菲利普斯学院唐氏奖学金(Tang Scholarship to Phillips Academy)带来的各项好处:四年学费全免,一次免费的夏季出行,每周发放20美元——可以用来买我心心念念的奇多(Cheetos)和指甲油,最后还有一台免费的笔记本电脑。
我以前一直没有自己的电脑,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将进入一个充满新可能的世界。据我所知,我是我所在的公立中学里唯一一个去精英寄宿学校读书的人,这感觉就像是被邀请加入一个门槛颇高的俱乐部。到达安多弗的第一周,我眼花缭乱于它的新奇和魅力,费很大劲才找到资助办公室,取到那台笔记本电脑;我给妈妈发了一张我抱着纸箱咧嘴笑的照片。回到宿舍后,我拿出自己的奖品——一台重量不轻但功能俱全的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它有着光滑的边缘和惊人的速度,让我惊叹不已。
但我与笔记本电脑的爱情故事却就此戛然而止。在图书馆里,我正在笨手笨脚地找地方,却看见朋友们都掏出了一台MacBook。每台都像张纸一样薄,似乎没有重量。而我的笔记本电脑重得让我背疼,还会像一只累坏的狗一样不停喘气,与这里明显格格不入。我原以为这台电脑是我进入安多弗精英世界的门票,结果却发现,它真真切切地暴露了我外来者的身份。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一直都是我在安多弗的难题:总是一名局外人。我跟更有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会因为与他们生活差距太大而茫然若失。当他们在布拉格或巴黎度夏时,我在纽黑文附近的众多二手店里忙着淘东西。全额奖学金与全额支付学费之间的差距让人感觉无法逾越。
但是,当我去参加面向全额奖学生的活动时,也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我父母上过大学,小时候家境也比我好,他们给了我许多文化资本,这是我的许多全额奖学金朋友所没有的。此外,我是个白人,能负担得起偶尔去听场音乐会或买副闪亮的耳饰的费用。全奖生都携带的那台隐藏含义丰富的笔记本电脑,成为朋友们认识我的基点。在家乡,我属于中产家庭,之后还成了让人艳羡的预科学校学生。但在安多弗,我突然变成了穷人。在努力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身份的过程中,我感受到阶级是多么的复杂易变。我的阶级与父母的收入有关,但它也植根于文化知识和被赋予更多意义的事物之中。
这就又讲到了那台笔记本电脑:高三秋天的时候,那台戴尔笔记本被用坏了,我又没钱再买一台。于是我设法从学校借了一台薄薄的Mac,之后便感觉周边的世界又不一样了。我期待以后发邮件的时候,都不用再考虑那个特权和权力的电子网。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焦虑:带着这台漂亮的电脑坐在华丽的食堂里时,我担心失去了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刚来安多弗时,这种始终处在斗争之中的紧绷状态就像一个陷阱:走到哪儿都会觉得不自在(学校也感觉到了,现在获全额资助的学生领取的是MacBook了)。但或许情况恰恰相反。或许我在文化上是灵活多面的,既能在安多弗百年礼堂的舞台上得心应手地介绍发言者上场,也能在纽黑文的纹身店里自在地穿鼻环。我清楚地意识到,戴尔笔记本掩盖了我的特权,Mac则隐藏我的财务需求,这让我明白了同学们看似简单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复杂的故事。我是一个受益于文化、社会经济和种族特权的全额奖学生:我的经历并不容易,但它依然是我的故事。
Laura Sega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凯特琳·麦考密克(Caitlin McCormick)是格雷戈里中学(Gregory School)的学生,计划就读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我母亲的格子围裙看起来像是金属盔甲》
图森
凯特琳·麦考密克(Caitlin McCormick)
每当面对服务业从业者,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会完全无视自己年幼时被灌输的礼仪。
过去17年里,我一醒来就会注意到这样的服务人员,注意到准备供应早餐期间裹在餐布里的叮当作响的餐具,以及从烤箱中取出的瓷盘。我会记得餐具垫被放在金属托盘里的形状、咖啡杯被倒扣以及弄脏了的布餐巾被撂在餐桌上的样子。
我知道永远不要穿着睡衣走到外边的公共庭院里;我母亲年复一年发出的嘘声让我明白,不能在客房的窗前高声说话。我成长于游客、教授和摄像师晨间压低声音闲聊的嘈杂声中。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习惯了那种适用于与陌生人寒暄的过度礼貌。
我是在一个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客栈里,在有着厚重的酒店业氛围的环境里长大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颇为憎恶。
我曾经没能准时去公园参加自己的五岁生日派对,只因为一位客人迟到了五个小时,而且连声道歉都欠奉。某个人住店一周,专门要求其房间每天打扫两次,却没有留过一次整理房间的小费。诈骗小企业的人光顾过几回。客人把床单弄脏,把厕所弄堵,把自己锁在房间外,然后要求打折。
服务业从业者和客人之间存在天然的权力失衡:我们用道歉应对冷嘲热讽。我们让顾客在他们吃喝住宿之后自行决定,服务人员在提供服务上有多用心。
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觉得我父母是极端的受虐狂,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所知的最不讨好的生意:也是教会我如何辨别权力失衡的生意。很快,我就在各种日常交往中注意到这种不公平。我开始明白,潜在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残障歧视如何充斥我们的社会——给小费如何只是“微歧视”的一个同义词。
我变得狂热起来。有时还很愤怒。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加入了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政治运动。我给参议员候选人拉票,给草根行动团体接听电话,担任南亚利桑那州女性基金会(Women’s Foundation of Southern Arizona)的董事会成员,审核非营利组织的经费申请,还为附近的儿童医院组织活动。
我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帮助别人的历练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一种新型的服务:公共服务。与此同时,我也做着黑色星期五的夜班零售工作,清理油毡毯上的呕吐物。当我把自己的第一份工资单拿回家时,从没见父母那么自豪过。
我最近发现的事实是,并非所有的服务都是天生平等的。看到客人因为接机出租车迟到而对我的父母大叫大嚷,仍然让我感到厌恶,尽管我每周也会花数小时时间做志愿者。但我从中学到的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高贵的,尤其是我们为他人做的工作。慢慢地,我母亲的格子布围裙看起来也更像金属盔甲了。我知道了如何欣赏父母细心倾听的天赋,他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客人没有准确提出的要求——不是给他们的茶里加糖,而是在他们等待一个电话会议时能有人跟他们聊天。我羡慕他们能那么自然地扮演胸有成竹的东道主角色,能带着微笑忍受各种恶言。
最重要的是,我钦佩父母一直相信人性,相信人们不会对不起他们提供的帮助。我意识到,学习给人们提供服务和学会相信他们极其相似。
Laura Sega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特雷邦是北地预备学校的学生,计划前往俄勒冈大学就读。
《在矛盾的夹缝中生活,我参悟了平衡的奥秘》
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
蒂莉娜·特雷邦(Tillena Trebon)
我生活在边缘地带。
我生活在这个树木为躲避大风蹂躏而缩成灌木的地方。我的家在郊区住宅、石头房子和泥巴木屋之间转换。
离开保留地和母亲一起去上班时,我看到了电话线杆的变化。保留地里的电线杆歪歪扭扭,之间胡乱悬挂着电线。进入我家所在的弗拉格斯塔夫时,电话线杆开始变得笔直。在我的一面,大自然是一种兴趣爱好。在另一面,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生活在郊区土地富余和农村土地匮乏之间。在这里,一望无际的天空和一成不变的草地,与公寓大楼和露天购物中心融为一体。
我在旱灾的边缘上保持平衡。
夏季,不下雨时,父亲的卡车开过后空中尘土飞扬。一层灰尘覆盖在野花和野草上。沉闷的大地上,烈火不断。浓烟窜入空中,如同在海上迷路的船只发出的闪光报警信号。人人都在祈求雨水。我们害怕每一滴水都是最后一滴。我们害怕环绕菲尼克斯四周的沙漠入侵。我们害怕热浪让树木枯萎,把它们变成仙人掌。
我生活在政治叙事的中心。在高中的走廊里和闹市区的大街上,气势逼人的自由主义与坚定的保守主义为敌,不断扩张。
天气暖和时,商店和餐厅会开门营业。身着套装的职场人士和梳着脏辫、穿着破洞牛仔裤的音乐人和艺术家相谈甚欢。他们一起抱怨旱灾,感叹滑雪季的短暂。
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共存的边缘。
在母亲家,我们在铺砌平整的街道上骑自行车、和邻居家的孩子玩接球游戏、用水枪打仗。
在父亲家,我们取水、喂马喂鸡、把狐狸从鸡笼旁边赶跑、看着野鹿在不到十码远的地方吃草、给花园翻地松土。当雨水、土壤、阳光和植物共同奉献出果实时,我们从藤蔓上将其摘下直接吃。
两家的墙上,都用传统的纳瓦霍织物和毕加索画作的印刷品作为装饰。
青少年时期的我天真单纯,成年后充满神秘。这也是一种困境。我知道自己必须迅速适应成年生活,把弗拉格斯塔夫生活的平衡做法留在身后。但我依然属于这里。在这里,截然相反的人和物相互融合,形成一种由矛盾构成的美好。我渴望只能在边缘地带找到的那些经历。随着自己步入成年,进入大学,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鼓励各种形态多样性的新地方,一个能让我学着平衡的新边缘。
Matthew Hint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阿巴比是布莱恩高中的学生,即将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就读。
《不属于我的家,庇护了我的梦想》
明尼苏达州布莱恩
乔纳森·阿巴比(Jonathan Ababiy)
我还记得6岁那年,光线填满宽敞的房间,我母亲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我还记得9岁那年,我常常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看迪士尼卡通片,电视机有过道内的冰柜那么大,放在墙上的一个山洞大小的内嵌空间里。我还记得12岁那年,每个房间都挂着在西班牙乡间拍的家人照片。我还记得14年那年,我在偌大的房子里一点点地给地毯除尘,折叠刚刚烘干的色彩柔和的衬衫。
我喜欢那栋房子。我喜欢阳光透过窗户倾洒进来的样子,仿佛可以扫清所有愁云。我喜欢自己总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面上找到一本书或杂志。
但我母亲使用的吸尘器不属于我们。我们从未付过有线电视费。照片拍的不是我的家人。我一周只能见到一次自己清理的地毯,我从未穿过自己折叠的色彩柔和的衬衫。那栋房子不是我们的。我母亲只是清洁工,而我是她的帮手。
大约20年前,我的父母以难民的身份从摩尔多瓦来到美国。我母亲做过许多种兼职工作,但我一出生,她就认定自己需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她在报纸上登了一份提供房屋保洁服务的广告,一对同为教授的夫妇联系了她。他们成了她的第一个客户,他们的房子成了我们维持生计的基石。经济衰退来了又去,但我母亲每逢周一和周五都要回到那里,有时周日也过去。
她整日戴着天青色的乳胶手套,操着蓝色的胡佛(Hoover)吸尘器,给仿佛有几英里长的地毯除尘。她擦过的所有镜子没准可以堆叠成那种由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打造的亮闪闪的摩天大楼。这对她来说并不新鲜。吸尘器和手套或许有些新鲜,但这份工作并非如此。在摩尔多瓦,她家里种有黄瓜和西红柿。她曾花无数个小时跪在泥土里,以教授指导学生的用心程度、以仁慈和积极主动的态度侍弄她的蔬菜。现在,她劳作的蔬果被吸尘器取而代之。
透过那两位教授的房子,可以一窥(更富裕的)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很少待在家,于是我便观察他们留下的痕迹:摊在厨房桌子上稍稍发皱的《纽约时报》,满当当的私人图书馆中翻到一半倒扣过去的书,总是停留在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我把这些痕迹当成由名人代言的通往繁荣之路。我开始从学校的图书馆往外借书,并经常阅读新闻。
他们的家是为我的梦想提供庇护之处。在那里,我这个戴着眼镜的电脑迷从《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上知道了一个名叫硅谷的神秘地方。在那里,我这个移民的儿子读到了一个名叫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年轻参议员立志做美国总统的消息——他也是移民之子。我从他们家看到过的生活告诉我,在美国,移民也可以成功。工作可以用双手来完成,也可以用头脑来完成。它让我对一种社会资本有了深刻的概念,我知道在美国可以使用这种资本。两位教授让我看到了他们取得成功的要素,我这一生都在试图做出自己的反应。
最终,吸尘器的吸力养活了我们一家。她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提醒着我,我为什么有机会开着叮当乱响的小汽车去上学。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的妈妈往美国梦的公式中倾注了太多劳动。她用蓝色胡佛吸尘器为我的生活撑起了一片天。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毕业证书为她撑起一片天。
本文整理自纽约时报中文网、美国留学那点事,转载注明原出处。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