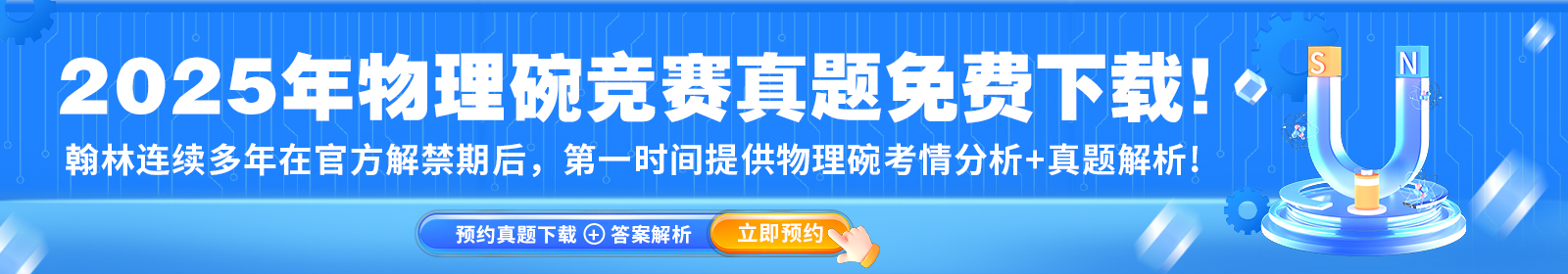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18岁我进哈佛时还不懂的事儿
1990年的春天,我16岁时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两年后,我18岁,在美国的奥数学术活动中拿了不错的名次,入围了1992年的西屋科学奖,怀揣着这样那样的奖项,走入哈佛大学的红墙。
所谓芳华正盛,怎一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能尽述。
2016年是我们96届毕业二十年。人近中年的校友再回故园,重聚在曾见证我们几百个青春时日的老教室里。
这是难得的一次将人生的得意与伤怀,尘世的纷乱与成败置于身外的畅谈。
聪慧依然的主持人抛出一个必是深思良久的问题:
”回首大学时代,你希望你当时就懂的事情是什么?“
毕竟多年未见,起初的问答都在得体与礼貌中轻缓而行:
“多看些书,多学门外语,能和往日的校友保持更多的联系。”
如此这般轮了四五个人,说了十几分钟,安全的话题已将将说完。一位短发的女同学此时抢过话筒,笑着答道:
“我希望当时懂爱,希望当时知道自己喜欢女生。”
有此坦诚和率真,之后的交流更多了些泪水与欢笑,激荡与顿悟。
Part1
人到中年,芳华已成追忆,该能更坦诚地坦白过往,也能更真诚地面对来日。
除去刷屏的票圈晒十八岁旧照,也可分享几件我希望自己十八岁时就知道的事情。
▼人生更像一首诗
虽然二十五年前在中文语境中还没有太多输赢在起跑线上的说法,可即便是在美国的藤校当中,也不乏把人生当作比赛的信众。
回想当年,同学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为GPA努力而纠结,都曾计算过哪门选修课的教授给分格外恩典,都曾费心费力地研读面试宝典或是考研题库。
毕业之后,或许随着阅历的成长,我们会按照成功学和励志讲师的布道,重复一句人生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这也不错,可我宁可当时就知道另一种看待人生的视角。
罗兰夫人在被法国革命吞噬前不久曾留下一句话: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诗,其中很多人扮演各异的角色,不到终点,难知因果。“
看到这句话的那天,我就爱上了其中的意象。
诗虽也讲格律,却远比比赛的规则自由灵动;诗既可鸿篇巨制也不乏短吟小令;好诗纵要酌词炼字却离不开冥冥天助。
诗才更像是人生的写照,也才是更值得为之付出的过程。
我们与他人远非仅是赛道上的选手,只为着跑向终点,也是交织牵绕的诗句,为彼此完篇。
如果当日就明白这一点,人生或许能洒脱豁达些许;今日明白这一点却也不晚,人生后程仍可活出诗意。
▼世界未必越来越好
1992年,福山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虽然那一年我没有看这本书,可在彼时,环顾四野,却难以怀疑他的预见。
那是个剧变连连的年代。
1991年的圣诞节,我和父母一起看着CNN直播戈尔巴乔夫告别的讲话。他合上讲稿的那刻,苏维埃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顶最后一次降下。
那时那刻,听着苏联歌曲、看着苏联小说长大的我的父母百感交集。
1992年冬天,第一张照片出现在了新生的互联网上,第二年夏天我用到了第一部便携式电脑,而在毕业那年已经能够在网上看到国内的中文站点。
整个90年代,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的融合似是顺着一个预定好的大叙述向前推进。
对于钟爱历史之人,那些青春岁月似是象征着历史告别了革命与纷争,世界自此走上繁荣锦绣的大同之道。成长于那个年代的我辈也自此坚信人性和社会都会向着善良与正义前行。
然而,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世界与这预期大相径庭。
在2016年对校友的讲话中,哈佛大学的福斯特校长也有此感慨:
“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对立和撕裂,世界上死亡、瘟疫、饥饿和战争重新肆虐,好似末日的景象。“
她以历史学家的广博视野安慰大家:
“380年历史的母校,见证过多少次如此的潮起潮落,她至今依然安健。”
那刻,坐在台下,我想的却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是500年或是1000年的周期,那即便如母校这样也未必常青。
虽然我还没有因为历史的跌宕变为不可逆转的悲观主义者,可不得不说,若是当年就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至于在愈发纷乱的世界中进退失据。
生于盛世,是无可厚非之幸,但惯于顺势则可能是我辈的阿喀琉斯之踵。
世界未必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心更需要勇敢与坚强。
▼年轻时可以耽误些时间 几周前曾读过一篇100000+的文章,其要义是:
“让我告诉你,人生的前20年是耽误不起1年,哪怕半年时间的。”
我在大学时代也深信这条定律。人生的规划要像钟表一样准确:3年幼儿园、6年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4年读博。
我心中羡慕的是大一隔壁宿舍的小弟—因为跳过两级,16岁就进了大学;
我不愿说出的鄙夷是那些不知道、不遵守时间表的行径,随意选课,更换专业,休学游历。
大学四年,按照这张时间表安然无事,也让我如期进入时间表的下一程,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可是在那里,时间表忽然失灵了。
或许是因为这已经到了可以列表的最后一段—博士毕业之后又会怎么样?此去经年,却没了可以作为刻度的标志。
或许是因为在同一条轨道上心无旁骛地走了十几年,却发现那并非自己所长。
时间表失灵的后果是彻夜的失眠、终日的焦虑和无法排解的抑郁与悲观。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危机,最后以耽误些时间方得化解。
我做了一件自己此前完全不齿的事情,休学一年,出去工作。离开原本的舒适区,发现的是全新的天地。
一个原本寡言、内敛和思辨的人,爱上了自己话痨、外向和行动的一面。与人相交、解决问题、成就不同,这些在耽误的时间中得来的,恰恰是没有时间表后人生所需要的。
我懂得这个道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事后庆幸在还还能耽误的年岁耽误了自己。
如果再晚几年,甚至十几年才明白,那选择的代价必定会高出许多。
▼理智以外,或许确有神明 我儿时接受的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传承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至上的信仰。
哈佛的训练更是要用理智来规范人生,每一名新生都要通过数据分析测试,包括逻辑、概率、统计这些学校认为无论哪些专业都必备的基本数理功底。
大一每一名学生的必选课是策论写作。我们每周读伽利略、达尔文、托马斯库恩的经典,用逻辑和分析来阐述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更无处不在的是哈佛的校训“真理”。
“发现真理,真理将让你自由。”
这是Harvard Yard红墙中一道大门上的铭文。每日进出,这句话也成了我心中的圭臬。
不过,怀疑的种子也是在哈佛埋下的。
Owen Gingerich教授在讲天文的视角一课时提到如果一系列物理常数中的任何一个变化1%,那我们已知的宇宙将不复存在,人类更无从出现。
在当时,我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但作为一个有趣的冷知识点却是记在了心里。再往后,见得多了,想得深了,自己也开始疑惑理智的局限和边界。
科学中的发现,即便是事后可以找到天衣无缝的逻辑,可想法的来源往往是“不可理喻”。有如电影《知无涯者》中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给人类留下惊人的发现,可每一条公式都来自于他近乎神一般的直觉。
真实世界中推动山河巨变的政商领袖,未必符合理智世界里优秀领导力的标准,却有一种难以抵抗的魔力凝聚千万人的力量。
在人工智能虎视眈眈觊觎人类理智的年代,我虽未接受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却愈发感受到超越理智的力量和信仰是人性与尊严最后的守护。
▼传承与自我毋需回避
我在中国的学生时代太多次被定义为烈士的后代,革命家庭的传人。虽是老师关注的焦点,却也难免被同学讥笑为靠着祖上的荫功而受了特殊的关照。
因此上,在美国高中两年后考入哈佛便成了一次自我意识的爆棚。
少年轻狂中认定除了自己的本事之外什么都没有靠,家族的传承从一个每日不绝于耳的极端走向一个被自己有意封存的另一个极端。
除去自家,对中国也有了种远观其美却不近前的微妙情感。
虽然终日醉心于中国的诗词书画,虽然常常流连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典藏,可与中国同学间却少了交往。
以至于日后在工作中遇到一位比我早一年的留学哈佛的学长,被盘问良久是否“伪造学历”。
这种矛盾之心在多年后才得以释怀。
2000年的夏天,我在长江边的奉节古城为我的祖父扫墓。晚间在县城的街上看着人流熙攘觉出了一阵难以抵御的活力。街边抄手店的婆婆竟还记着祖父牺牲前后的情形。
我从未生活过的故乡自此变得真实。
我该是那个时候终于下了要回中国的决心,自此传承与自我才慢慢地重回一处。
再多年后,当我自己的孩子到了懂事的年岁,问起我祖辈的往事,我才明白传承是无法回避的。
Part2 从我十八岁到2017年岁末,二十五年过去,虽然知道了当时不知道的事情,可未必有了更多的智慧与定力。
周围同龄人和整个世界中焦虑日显,乱象丛生,乃至有智的长者都要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来自勉。
岁末年初,我们寄希望于日月经天、冬去春来这样的自然恒率能带来更美好的明天,岂不知有些年不但没有春天,甚至都没有夏天。
有些道理我们在18岁上不懂,到了不惑之年可能仍然不懂;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们却不能不思考。
2018年,我们该思考些怎样的问题?
▼富强之后路在何方
2018年,富足对于个人不再是奢望,强盛对国家已在眼前。
我有幸仍能见到1920年代的耄耋长者,他们欣喜自己毕生的奉献带我们走到当下。
这之后要靠我们,路又该怎么走?
在生存和追赶已不是唯一目标的时代,人生的意义何在?还有什么能给我们鼓舞与动力?
▼技术将怎样颠覆未来
今日,面对技术颠覆,已是人人自危。但全新的未来是怎样,却鲜有人仔细思量。
若为后世计,那现在就该细细推演一番那个未来世界的模样。
当资本因为泛滥而失去往日的光辉,资本主义还能否存在?
当铸币权和话语权被重构,政府与社会结构还能否稳固?
当技术引发人类自身思维能力的萎缩和神经结构的变化,人性和价值观还能否存续?
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成就、财富、荣誉失去了根基,又该如何重塑自己?
▼焦虑与幸福能否超越
焦虑和幸福是今日最高层面的话题,却也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便提出的设问。
技术和全球化让焦虑和幸福在更快的时间和更大的尺度上交叠,却仍逃不过人生苦短、幸福无常的感叹。
焦虑是否是人类的常态?
幸福是否是生命最高的追求?
知天、懂爱、识己之后是否能超越焦虑与幸福而做好生活的准备?人生应如何成就不同。
人或贵重或平凡,在世人眼里看来的成败,或许真是五成在时势、三成在境遇、两成在自身。
以此而看,纵使是文治武功的唐宗宋祖也未必造就了多少不同,因为那只是有此境遇的帝王本就该会去做的。
人生的精彩和后世的评说该使用怎样的标尺?
如果我们不在意于互比成败得失,是否更应该去思考同等的时势和境遇之下,我们成就了怎样的不同?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审视,有负此生”。
新年伊始,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但唯有思考,才能不负这个时代,不负此生,更不负来者。
2018年,我们与诸君共勉!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