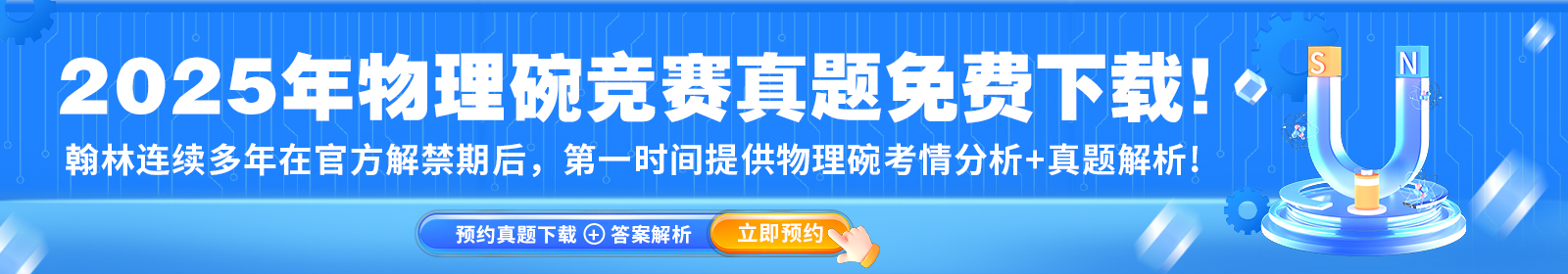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从全民热炒到打入冷宫中国奥数真的凉了吗
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术活动(IMO)中,我国6名参赛选手全部夺得金牌,并以227分的总成绩夺得第一。对不了解的人来说,这个成绩仿佛理所当然——中国本来就是奥数强国啊!但其实,中国队已经有整整4年没有拿到冠军了。
不但没有冠军,而且有时还和第一名分差不小。冠军的错失,与全国范围内的奥数热退潮有关;而奥数热的退潮,又和这样一个扎心的问题有关:为什么我国拿了那么多奥数金牌,却没有培养出真正卓越的数学家?“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菲尔兹奖(数学诺贝尔奖)”,成为了继“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诺贝尔奖”之后的第二个灵魂拷问。
以菲尔兹奖来说,2000年以后的14位得主中,至少有8位获得过IMO金牌。但至今,在获得金牌总数最多的中国,却还没有一位中国籍菲尔兹奖获奖者。这一切确实让人生疑:是奥赛金牌的含金量不够,还是我们培养数学家的思路出了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说得小一点——事关民族尊严,我们不要面子的吗?说得大一点——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有一整代人,用了错误的数学学习方式。而数学,是科学发展的根基。其实当我们回望中国的奥数历程时会发现,它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有意思。其中有疯子,有天才;有疯狂的巅峰,有落寞的低谷。不仅如此,在数学的世界里,有些人看似是疯子,但其实却是天才;而有时你以为已到谷底,其实却是黎明之前。
在年长一点的朋友心里,奥数和普通的兴趣班是不一样的:奥数,是我们的民族天赋,是中国的标签。它长在我们这个内敛民族的血液里,是曾经为数不多可以让我们抬头挺胸的话题。
其实,在中国,1985年前,还没有多少人听说过IMO奥数比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为中国人拿到了第一块奥运会金牌。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大国尊严”,有时候是凝结在小小的金牌上的。;
正巧,198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有人问中国代表团,为什么所有大国都参加IMO,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一直不参加?
这句话深深击痛了刚刚拿到奥运金牌的中国人的内心。
中国政府当即决定参加当年的IMO奥数比赛。但因为没有准备,仓促备战,只派出两名数学成绩优异的中学生作为选手。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随便两个中学生,就能和全世界的奥数尖子一较高下了?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没当回事,但是奇迹发生了:来自上海的中学生吴思皓,还真的拿回了一块铜牌。别人全力做到的最好,还不如我随便搞搞?我们收获了信心,随后,便是倾尽全力的准备
1986年,中国便开始组织冬令营,从各省、市、自治区广泛选拔IMO选手,并建立起“冬令营—国家集训队—国家队”的选拔模式。;
这个模式的效果,好到猝不及防:在当年的波兰IMO奥数比赛中,我国选手成功拿下3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总分居第四,成为全世界最闪亮的一匹黑马。许多外国领队都纷纷预测:中国队很快就会拿到第一名。万万没想到,真的很快。仅仅3年之后,1989年,第5次参加IMO比赛的中国,就拿到了总分第一名。
1990年,中国还首次获得了国际奥数比赛的举办权。仿佛开了挂一般的神速发展,让奥数成为了全民话题。这场比赛成为一场全民关注的盛会,从赛事筹备,到选手挑选,社会各界广泛支援,人人恨不能参与其中。
最后的结果也不负众望,我国以5枚金牌、1枚银牌的好成绩,拿下总分冠军。从今天的眼光回看,那是一个数学天才比流量明星更吃香的年代。1990年,在十七八岁就获得奥数冠军的高中生们,成为了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小鲜肉”。比如年龄最小王崧,就被称为是“最像数学家的冠军得主”。;
在他就读的黄冈中学,多数师生也把王菘看作是陈景润那样的天才。
而王崧不修边幅的外表和怪异的性格,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的想象——这就是“数学天才”的气质啊!哪个数学天才不怪呢?;
他的老师回忆:“王菘老是拖着长鼻涕,也不擦。上课时一定要把耳朵贴在桌面上,不看黑板,好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听得极其认真。”
王菘思维跳跃,解题方法出人意外,辅导他的老师都要琢磨很久才看得懂。;
但王崧也因为过于天才,而遇到过烦恼。在1990年的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中,因为题目太简单,王菘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反而没能获得入选资格。
但幸运的是,当年因为是我国举办IMO,怕挑不到出众的选手,所以破天荒地进行了第二次选拔。;
第二次学术活动的题目极难,王菘发挥出色,终于C位出道。;
最终,王菘以41分的成绩拿下了一枚奥数金牌,离IMO的满分仅一分之差。;
得益于当时全国奥数热潮,王菘还得到国务院总理的接见。“数学天才”成为了大众偶像,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和王崧一样。
凭良心讲,我赞同大家追数学天才的星——总比追流量明星好。只是,对数学的崇拜和追求当然是好的,但任何事情过了度,都要被反噬。过犹不及。今天我们知道,IMO主要是个人奖项,代表的是选手个人的成绩,未必和国家的数学实力等同。;
但当年,金牌得主回到家乡之后,往往被视作“为国争光的英雄”,受到各级领导的亲切接待。;
从参赛选手到辅导老师,也会收到丰厚的奖金,有的甚至直接分房。;
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下,奥数学术活动的热潮渐渐兴起,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此后数年,王菘这样的“数学天才”不断涌现,但是他们的故事,却常常令人唏嘘。;
2010年,数学天才、两届IMO奥数金牌得主柳智宇,出家了。
这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比他两次获得IMO奥数金牌、保送北大、拿到MIT全额奖学金,都更轰动。而柳智宇背着父母出家的过程,全程安排妥帖,严丝合缝,宛如一道完美的数学题。回到2003年,柳智宇凭借优异成绩进入华师一附中理科实验班。
高三那年,他拿到北大数学学院的保送资格,并入选奥数国家集训队。10余年后,柳智宇的高中数学学术活动教练余世平仍然认为,他是其所有学生中“脑筋最灵活的”。
华师一附中是湖北省首屈一指的奥数学术活动强校,但当时还未出过一位奥数金牌得主,整个学校都对柳智宇寄予厚望。
但此时,柳智宇却已萌生退意。
长年机械的答题培训和紧张的学术活动,已将他对数学的兴趣消磨殆尽。加上长期过度用眼,他几近失明。
走路时,他必须不断眨眼才能防止摔倒。
即便如此,他还是日复一日地做题,似乎只有将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才能忘记眼疾的侵扰和外界的重托。;
但内心长久的困惑却按捺不住——他不断追问自己,这样的训练有什么意义?
国家集训队在沈阳封闭训练时,校长特地从武汉飞去探望柳智宇。
饭桌上,柳智宇突然对校长说:“我个人不需要这块金牌,是你们一附中需要。”
柳智宇控诉学校“太功利、太世俗”,把学生当成了争名夺利的工具。
校长蒙了,赶紧让数学教练联系他的班主任文勇,告诉他:柳智宇现在不想搞了。
文勇揣摩出了柳智宇的心思,叫他回校上课,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一周之后文勇才找他谈心,跟他聊了很久尼采的哲学,最后才告诉他:你今后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平台证明自己。
柳智宇想了想,答应回到国家集训队。
那年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学术活动,全世界总共3个满分,柳智宇是其中之一。
但他并没有像身边人那样欣喜若狂。
回顾这一路,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太多。
在全民奥数的狂热中,选择学术活动这条路其实比高考更残酷。很多缺乏天赋或运气的人,努力了很多年,到头来才发现此路不通,转而回去参加高考。
与柳智宇这样的成功者相比,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陪练”。
柳智宇一直对身边出局的同学抱有同情。在他拿到北大保送资格后,曾好心地问一位失利的同学:“我要怎样才能帮助你?”
那位同学的回答却令他很郁闷:“我需要的就是做更多的题目,你的帮助对我不是很重要。”
其实,因为激烈的竞争,同学之间早已经有了嫌隙,可能只剩下柳智宇没有发现。
有一次他因为指出某同学的错误,在网上受到对方攻击,称他为“傲慢的伪君子”,“总拿着一套道德说教去批评别人”。
柳智宇没想到的是,这位同学的话,竟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还有一次奥数比赛获奖后,柳智宇的照片和获奖喜讯贴在学校墙上。第二天,照片上的头就被人撕了下来。
不仅是同学,和父母相处,柳智宇也常常感到压抑。;
虽然在父母看来,柳智宇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对他无微不至的保护是为他的前途着想。
但柳智宇却觉得不堪重负,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盛放的空间。;
据说,刚进北大时,他母亲会定期从武汉来给他洗衣服。GRE考试前一天,母亲跟他一起去考场踩点,第二天还目送他进入考场。
或许是肩上的期望过于沉重,也或者有太多问题想不明白,大学期间,柳智宇狂热地迷上了佛学,并成为了一名佛教徒。
父母得知他有出家的想法后,遍寻了柳智宇的师长,希望劝他把心思放回到数学上,但没有成效。
柳智宇了解父母的担忧,也有些愧疚,但他并不打算妥协。相反,在发现争辩无用后,他学会了表面顺从。;
比如母亲叮嘱他“身体寒,要多吃羊肉”,长期吃素的柳智宇就去食堂点上一碗羊肉面。;
申请出国也被他视为“报答父母的恩德”,父母让他考GRE、读美国新闻、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章,他一一照做。;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附全额奖学金。父母高兴极了,盼望着儿子走上数学家的道路。;
但他们没有等来儿子踏入MIT大门的那一刻。等来的,是“北大数学天才遁入空门”的新闻。;
其实,参加完北大毕业典礼一天后,柳智宇就给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Gigliola Staffilani 发了邮件。;
“很抱歉地通知您,我不会成为MIT的学生了。您可能会很惊讶,我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佛教,并成为北京龙泉寺的一名僧侣。”;
发完邮件,柳智宇打包行李上山。
父母立刻从家乡武汉赶来劝阻,一番争吵后,强行把他带回了家。;
父母为他准备了两个去美国的行李箱,安排好到波士顿接机的向导。;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临行前一天,柳智宇告诉父母,他想到北京和同学们道个别。第二天中午,父母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
从小听话,被视为“数学天才”的柳智宇,就这样出家了。
舆论中常有人说他是被奥数“烧坏了脑子”,无法面对正常生活,所以选择出家。;
这种说法当然有偏见,但因为那些年类似的例子不少,而柳智宇的经历又极为传奇,所以以讹传讹。谈到中国奥数时,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数学王国里有座天才云集的疯人院”。;
天才和疯子,有时似乎只在一线之间。像柳智云这样的人,少年成名,被寄予厚望,之后却似乎陷入“疯狂”,令人惋惜。;
而事实上,要疯了的人又何止他们?;
就在这个月,有一句话流行起来,叫做“我太难了”。它有一个衍生的段子是这样的:“我上辈子肯定是一道数学题——我太难了。”今年更早的时候,还有一个这样的段子,也上过微博热搜:;
“友谊会走散,爱情会变淡,困难会让你痛苦,生活会使你屈服……“只有数学不会,不会就是不会。”
数学,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准确地说,是童年阴影。数学家王元记得,北京第一家奥数培训机构是在1985年出现的,那是中国首次参加IMO之后不久。;
该机构宣称:“所有任课教师均通过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一级教练员考核”。;
那时,奥数还并不为大众广泛接受,社会上还流传着“数学学术活动是中小学生搞搞的智力小测验”,“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搞数学学术活动,是不务正业”等说法。;
可是,1990年IMO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随着奥数热度暴增,许多学校开始将奥数成绩作为评判学生智力、能力的重要标准,于是催生了大批奥数培训班。;
据统计,当时各级教练员人数达到6500人左右。即使这样,各类培训机构门前仍然挤满了学生和家长。;
可以说,只要谁声称自己是奥数教练,就不愁没有生意做。;
1998年,“小升初”取消统一考试后,奥数成绩的参照意义更加突显,这等于给冒出火苗的“奥数热”加了一个鼓风机。;
原本是一种考察青少年数学天赋的学术活动,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蜕变成考取好学校的敲门砖。;
这就是“奥数经济”。 举个例子:有媒体估算,2016年,杭州小学生在奥数培训上一年的支出,即达3亿元。;
举办学术活动能带来高额回报,浙江省的“睿达杯”在2016年有约18万名考生报名,其中4.6万人参加复试,按照初、复试各交30元的规定计算,仅报名费即可得600多万元。;
而为在学术活动中拿奖,家长还要让孩子参加训练营、冬令营等,交纳成千上万的费用。但其实,这样的“全民奥数”并不利于选拔真正的数学人才。;
赵斌曾担任中国队副领队,于2016年带领浙江省队参加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他曾感慨:杭州地区2万多报名者中,或者真正适合参加奥数培训的不到5000名。 这多出来的1.5万人,大多数是不喜欢学奥数的,他们的成绩也许能够通过培训得到提升,但大大地浪费了时间和教育资源。著名的华裔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丘成桐,曾毫不客气地炮轰:“做奥数学术活动绝对成就不了数学大国。数学其实是在做研究,而奥数却只是在做题。”作为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丘成桐回忆起老师与“奥数”的一段往事。那时陈省身教授还在南开大学任教,有一些孩子手拿着“奥数”的题目来请教他。陈省身看了看说:“不会做。”;
丘成桐想说的是,出“奥数”题目的很少是一流的数学家,而且这些题目出得很偏。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期间,丘成桐带了许多从中国内地考去的学生,其中许多人就曾是“奥数”金牌得主。但是这些被
中国教育界视为数学天才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合乎丘教授的要求,全部需经重新训练后才能开始数学研究。;
有柳智宇们炮灰在前,又有丘成桐们炮轰在后,整个社会对于奥数的批评和质疑,越来越激烈。;
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在努力遏制这种狂热,在2001年、2013年和2015年,教育部多次发布“奥数禁令”。翻开2013年以后关于奥数的新闻、评论,几乎全是一水地批评。;
终于,2018年3月,教育部下达《通知》,全面取消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学术活动、科技类学术活动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才从根本上斩断了奥数的“需求”。;
曾经大热的奥数学术活动一下子被釜底抽薪,打入冷宫。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近几年,我国在IMO奥数比赛上成绩的下滑。;
中国奥数,真的会“凉凉”吗?讲到这里,你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今年的IMO团体第一名,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全民奥数退潮以后,我们的奥数水平仍然维持在了国际顶尖水平。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近几年,与其说奥数是被打入了冷宫,倒不如说,是有了自我调整、回归理性的时间。2018年,带头炮轰奥数的丘成桐教授,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丘成桐数学英才班”。
坚守“宁缺毋滥”的原则,数学英才班2019年招收人数不超过20人。北京大学类似的“数学英才班”,2019年招收人数也不超过30人。;
没错,就是前面带头喷奥数的丘成桐,怎么一转头,丘老又带头搞起了数学英才班?;
其实,这并不矛盾。在丘成桐看来,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奥数获奖者,而是那些真正有天才的数学研究者。奥数本身,并不属于高等数学。一个在奥数学术活动中获奖的学生,如果有意从事数学方面的研究,还须在大学、研究院进行更系统的学习。;
从这个层面讲,奥数培训的大众化是根本不必要的。丘成桐本人,生于1949年的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22岁就获得博士学位,34岁时荣获菲尔兹奖,之后又拿下沃尔夫数学奖、克拉福德奖等世界顶级大奖。
他知道,对于学习数学的学生来说,重要的不是习惯于用已知的方法解决别人出的问题。重要而是,自己去发现问题,并找到新的解决方法。;
只有那些真正在思维方式层面获益、而非为掌握解题技巧所困的优秀奥数选手,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最重要的是,经过这样训练的人,即便不从事数学专业工作,也可以在其他领域有所成就。从1988年起担任中国奥数国家队教练的熊斌曾直言:“在中国,只有5%的学生适合学习奥数”,因为“真正数学学得好的人,不是学出来,而是悟出来的”。尾声人人都知道,过犹不及。但是问题在于,“正好”很难。但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再难,还能难过数学?
全民奥数已经被证明要不得,一刀切地禁止奥数也不行。归根结蒂,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奥数该不该学”,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学生的潜力,让他们体会不同学科的乐趣,变成更优秀的人。拥有天赋和实力的数学天才一直都在,他们需要等待的,仅仅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机遇而已。我们需要数学天才,却未必一定需要数学学术活动,因为学术活动只是一种手段。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灵魂拷问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菲尔兹奖?其实,菲尔兹奖与IMO比赛的相关性确实很高。
据知乎答主@卢旺杉的统计,从1990年算起,每届获奖者中都会有至少1位是20年前左右的IMO获奖者。而中国队虽然总是得总分第一,但是要到差不多2000年开始,才有选手获得个人第一名。
数学的世界里,其实是没有“团体冠军”的,但凡要有突破,依靠的是个人的顶尖才能。所以,如果从2000年开始算,那么20年后,是2020年。如果你对数学圈比较熟悉,2010年和2012年,中国分别有两位同学拿到了只授予青年数学奖的顶尖奖项拉马努金数学奖。一位叫张伟,一位叫恽之伟。当你以为我们在奥数的低谷之时,也许我们正在顶峰。中国的菲尔兹奖,也许不是没有实力,只是时候未到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