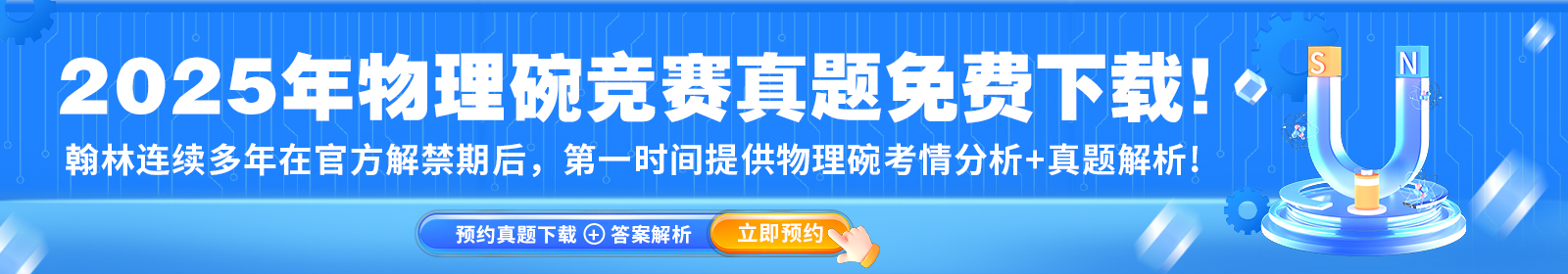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从竞赛到择校为什么总是奥数
1938年的春天,昆明北郊的陈家岩黄沙弥漫。此地缺衣少食,但位居祖国大后方,终究远离了日机的轰炸。闻一多穿戴整齐,迈步走出平房,迎接跋山涉水前来投宿的大数学家华罗庚。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华罗庚一家六口人,共同“蜗居”在这昆明城窄小的屋檐下。入夜,窗外是清澈的繁星,大大的客厅被一道床单分为两半,两家人笑着、聊着,缓缓睡去;白天,闻一多抬头吟诵着唐诗楚辞,华罗庚埋头研究着代数几何,两人偶尔相视一笑,清贫的生活不改学者一丝不苟的学风。1946年,华罗庚去苏联访问,临走前嘱咐闻一多道:“情况这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要多加小心才是。”闻一多的回答得十分英气潇洒,想不到二人就此天人两隔。
华罗庚坐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卖报童吆喝着新报的头版头条。他瞬时目瞪口呆,抢过来一睹,已是眼泪横流,挥笔写九一首《哭多》,末尾一句云:“魔掌竟敢杀一多!”
可惜如今,这样有血性、有文化、有性情的华罗庚无人知晓,留下的只有被孩子们视为童年阴影的“华罗庚数学”和“华杯赛”。如果华罗庚目睹今日之景,应该会皱紧眉头、一言不发。他在1956年就大声疾呼:“数学学术活动的工作会不会打乱学校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全面发展的原则呢?做的不好,是有可能的。”
但事实是,在巨大的升学焦虑面前,没人能听得进华罗庚先生警示的言辞。
奥数的狂热是每个人都想要的结果:国家借此选拔有创新力的人才,学校借此获取尖子生维持升学率,家长借此来实现保证子代教育质量并谋求阶级跃升——这是它提高效率的一面。
然而,奥数的狂热又带着某种原罪:国家还要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学校不能变相搞小升初考试,家长对“奥数不拔尖就完蛋”的潜规则感到愤怒——这是它阻碍公平的一面。
于是,奥数既是所有人私下里都想染指的奖杯,却又要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它的唾弃和鄙夷……这种态度,就好像一个男人在谈论他的初恋。
华罗庚先生怕是怎么也想不到,他在1956年一手创办的中国数学学术活动,竟渐渐地异化成全国80%小学生每周花十几个小时才能应付的梦魇,以及每个家庭年度支出上的巨额数字。
问题是,奥数是如何一步步“异化”成这个样子的?为何是它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而非语文、英语?又该如何理解奥数过去“屡禁不止”的现象?去年起,“禁奥令”真的来了之后,新兴的“逻辑课”、“数理思维课”,究竟是不是对奥数的重演?这些问题,都值得被认真地解答。
“一边倒,学得好”:1950-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骤然分为美苏两极。50-70年代,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前苏联一直在军工业方面领先美国。
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战……纷飞的炮火只是美苏争霸的表面,在华盛顿、底特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指挥部与工业重镇中,一场“内功”的肉搏正在无声无息地进行:数学与计算机。
热火朝天的军备学术活动背后,实际是一路狂奔的数学学术活动。哪个阵营的青年能更好地抽象思考、迭代系统、处理大批信息,谁就能最终获胜。
美国——这个彼时最现代化的国家花了20年时间,做了一场大错特错的实验。1960年代,他们大改中学生数学课本,激进派怒喝:“我们的数学课除了定义和计算题,能不能学点有用的东西?!”于是,能帮着造飞机和太空船的微积分、概率统计、逻辑学等被全面下放到中学。这在历史上称之为“新数学”运动。
这场运动自然引发了轩然大波。保守派数学家在教育部会议上一脚踹开凳子,指着激进派的鼻尖痛骂:“你们这么搞,干不过苏联佬!那帮学生,连基本概念都不懂,拿头去思考?不过是一群高级产业脓包!”
十年后,在巨大的压力中,“新数学”运动被叫停。面对一代青年被毁掉的基本功,保守派又引领美利坚走向另一条错误的道路——“回归基础”。于是,中学生们变本加厉地写了10年加减乘除运算题。
目睹他山之石,想必各位均是倒吸一口凉气。我们只能期望,类似的历史不要落到我们的下一代头上。今日的世界变得更快,20年的学费,我们交不起。
当美国在一路折腾时,苏联人的大脑却一直清晰。1953年,教育家柏拉基斯在《数学逻辑能力的培养》中写道,数学教学应该遵守以下四个原则:
1、严格保证学生理解每一个概念,具体到定义里的每一个字。
2、严格保证学生理解每一个定理、公式的成立条件与结论。
3、严格保证学生亲自证明过全部结论。
教员在讲解中无论何时都不能违反这三个规则,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同学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新中国早期的数学教学,跟随外交政策一起“一边倒”向苏联,学到不少好东西。1957年,中国的《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修订草案)》颁布,里面写道:1、 中学数学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基本概念和观念。
2、 除了教知识,更要教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极力避免让学生记忆大量的次要公式和法则的情况。
4、 必须培养学生使用算表、计算仪器、测量仪器和绘图仪器的技巧。
里面的每一条,都足以令我们汗颜。
那个年代的数学教学,在实践过程中也领先我们几个身位。
1953年,华罗庚跟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再次到苏联访问,苏联数学学术活动主办方握着他的手说,数学学术活动不是为了评奖,而是“引导青年人进入科学的最先一步,鼓舞青少年训练‘research ability’(研究能力)的起点”。
又历经几年筹划,1956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4个大城市举行了中学生数学学术活动。华罗庚先生兴奋地在《数学通报》上欢呼:“中国即将拥有自己的数学学术活动协会了!”
当时的数学学术活动教什么?据一名亲历者回忆:“那时有一些数学家,如华罗庚先生,给我们开讲座。有的讲国外数学发展的动态,很有趣,有的讲数学公式和定理的推导。我们几乎不做难题,华罗庚先生还限制我们做题,说一旦考试等于模仿做过的题目,就失去了探究的价值。”
这批学生中,最后有一部分特别热爱数学的走上了专业道路,发展得非常好。
这种“优哉游哉”的氛围,不由得让人联想起西方古代才有的自由学园。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聊聊天、思考数学与哲学的问题,不在乎迅速成才,更不可能揠苗助长,要的就是在成长中慢慢“悟道”。
越是物质贫瘠的时代,好像越容易以简单的空间孕育出硬核的思想。
如果奥数这样下去,它自然不必成为全社会的焦虑,而只是一项有益于少部分天才的补充性教学活动。
然而,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奥数也就此变了模样。国家要想实现这条东方巨龙经济、思想的迅速崛起,必须有大批高智力人才的供给。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寻找天才”的运动正式开始。
而当中国渴望批量性地复制、催熟天才之时,奥数学术活动就成为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选拔机制,也就此拥有了本不该属于它的广阔舞台。它从少部分天才的“加餐”,变成广大学子迫于选拔压力不得不吃下的“催熟饲料”。
当奥数从一种超凡的素质跌落为升学所必备的工具,这就宣告它必将走上“异化”的道路。
毛主席在1942年就说过:“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 ”
恰好在那个时间档口,属于《毛主席语录》的时代彻底过去了。新时代需要的,就是把每个少年拎到半空中,凭空提高。
冲刺!IMO金牌:1978-1995
1983年,美国,来自中国的花季少年车晓东以满分成绩获得了第34届中学数学国际学术活动的冠军。这副纯真的东方面孔被境外媒体围得水泄不通。记者问道:“在中国学奥数,这么多年,你快乐吗?”面对西方媒体略带挑衅的提问,车晓东昂首挺胸回复道:
“我开始跨入数学大门之时,我的祖国的科学环境刚好重生。我去听了几次特别有趣的科普讲座,还有关于科学家和神童的介绍,这让我特别渴望学习科学。虽然这要放弃很多玩耍的机会,一个人孤独地关上房门学习,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它和玩耍一样特别有趣!”
那是一个号召天才们纵情发展的时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70年代末,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科学、教育重获新生。无数顶尖教授出于民族责任感,来到各大中学做科普讲座,甚至选拔合适的人才跟随自己提前学习。
“车晓东们在哪里,请迅速把他们都给我找出来!”在一个奋发向上的时代,人们想要改变祖国的愿望足够强烈,但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便将希望寄托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国家教育战略上。
1980年,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成立。有了专业机构的支撑,我国的数学学术活动取得了飞速发展。从省到各区县的各项赛事逐层铺开,学习奥数成了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事。
家家户户都在想,万一学得好,保送清华、到哈佛深造,学成归国改变世界,那可不得了!
80年代中期,国内的数学学术活动初具规模,这些在国内拿到金牌的青年学子们,也渐渐有了一个更加伟大的梦想:我们的数学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们要走出国门去,和美苏的同龄人试比高!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术活动(IMO)的金牌,就此成为中国人魂牵梦萦的下一个终点。
IMO
或许是由于数学与“信息”和“军事”这两个综合国力的指标密切相连,一直以来,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术活动都是全世界规模、影响最大的学科学术活动活动。
1985年,我国第一次参与国际数学奥赛,但是被虐得头破血流,只获得一枚铜牌。1986年1月,中国第一届国际数学奥赛冬令营在南开大学开营,自此形成了“冬令营——国家集训队——国家队”的队员选拔模式。
这届国家队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展现我国学生对数学的热爱”这么简单,它要肩负起两年前许海峰为祖国拿到奥运会首金一样的使命——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了,还站得很高、很高!
在没有战争的年代,奥运会与奥赛,就是刺刀见红的战争。
在冬令营里,每个队员要做的很简单:凡是数学奥赛曾经涉及过的数学板块,必须统统学会,不准有丝毫漏洞。先苦后甜,那一年的国际数学奥赛,中国代表队意外获得3金、1银、1铜,直接跻身世界四强。
1990年,第31届国际数学奥赛在北京举行。由于我国第一次承办该赛事,所以受到极大的重视。在充分的准备下,中国代表队以5金1银的彪悍成绩,成为全世界第一!比赛后,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代表团成员,由新华社采写的队员故事被收入国家语文教材……
家家户户欢呼雀跃,家长指着报纸对孩子说:“宝贝,你也该像他们一样,念中学时就能为国争光!”于是,华罗庚金杯小学比赛的报名人数,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奥数就是综合国力、教育质量和国人智力写照”的潜台词下,奥数金牌的多少支撑起国民关于祖国实力的想象,也就此成为民族尊严、民族骄傲的晴雨表。
夺取金牌,毫不意外地演变成政治任务,甚至有部门要求奥数代表队“像女排学习,拿下五连冠,迎双喜临门!”
耐人寻味的是,奥数在80年代的发展,与行政权力还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有着极大的关系。但也正是在与政治和民族情绪打交道的路上,奥数失去了它本来纯粹的面目。
1994年黄冈中学校庆前夕,时任校长的曹衍清难以入眠。由于学校在国际数学奥赛贡献了“2金2银1铜”的光辉战绩,70多家中央级媒体纷纷派专人从北京赶来黄冈采访。新华社记者头一天晚上就写好通稿,第二天一早,“黄冈荣耀”响彻全国。
当晚,曹衍清坐在电视前收看新闻联播,黄冈中学校庆是第五条,口播。他舒了一口气,这下,不仅校史上又添了一个重磅时刻,接下来很多年的小升初和中招,又变得轻松了一大截。而这个几个学生,都要被清华和北大抢着要了。
当奥数金牌等于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各省教育局的奖金、保送清北复交的特权;当在全国奥赛获奖都足以“降到一本线录取”、被重点中学免试;当奥数金牌从国家级的任务变成各省教育局的政绩、各重点中学办学水平的标志、家长择校的主要参考……
学习奥数,从此与知识无关,没拿到奖牌,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进入90年代,一个孩子即使在小升初考试中成绩平平,但只要在数学学术活动上获了奖,都会受到重点中学的优先考虑。
之所以如此,一位中学校长的想法非常有代表性:“经过严格数学思维训练的学生,将来在学习中,尤其是理科课程的学习中会表现出较大的潜力。”
可惜的是,这些数学得奖的孩子,并没有多少经历过严格的数学思维训练,大多数人只是被强迫着多做了几本奥数题而已。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92岁高龄时,为青少年数学爱好者题词:“数学好玩”。
“好玩”是陈省身对数学的切身感受。一旦数学与升学等功利因素脱钩,奥数便能回到本真的状态,能够吸引真正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参与。
但先生的想法,在校长们看来,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美梦罢了”,毕竟“学校每年都要招生,也每年有人毕业。我要让这所学校一直活下去。”
明目张胆的作弊游戏:1995-2007
1992年8月,在加拿大举行的第七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上,有不少教育学者站出来反对奥数:“数学学术活动只面对少数天才,会不会忽视大多数人?过早的专业学习会不会妨碍青年的全面发展?竟赛题多为偏怪难题,与日常教学是否脱节?”
90年代中期,第一届少年班(1978年招生)的成员们步入中年,他们有的混得不错,挣钱的挣钱、读博的读博。但另一方面,这些神童们在情商和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逐渐爆发出来。
当然,天才本来就是“古怪”的。不过渐渐地,一种好的声音——“不超前才是健康成长”——开始逐渐唱响。
然而,就当奥数开始面对家长的反对与声讨时,国家一项意义重大、目标积极的教育改革——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遍推行,却给奥数这把渐微的火种狠狠地续了一把命。
90年代末,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部门为了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可没了统一考试,重点学校还要选拔尖子生。于是,奥数奖项作为“智商评级”的等价物,其重要性再度发酵。历史的复杂性,在这个案例中被充分地体现。
从此,奥数不再是天才们为国争光的光荣使命,而是每个孩子为了能进入重点中学所必须作出的巨大努力。
取消小升初统一考试,却取消不了“选拔”的本质。在追求“人上人”的路上,孩子和家长们踏上一条不归路,越走越远……
为了选拔尖子生,一些知名的公立中学,比如人大附中、实验中学、北京四中等等,率先建立起自己的“坑班”。坑班一般从三四年级开始,每周上一次课,数语英都讲,每学期考一次试、重新排班。
一二班的学生可以高枕无忧,到六年级时,重点中学便会主动与他们签约;而末尾几个班的学生,家长急得四处奔走,询问究竟几班可以签约,还要寻找其它学校的录取政策……
家长们很少知道,尽管学校披着“全面发展”的幌子,讲数学、语文、英语三科,但在最终排名时,数学的权重远远超过50%,甚至达到80%以上。而这么做的原因,主要因为数学无法准备、无法“套作”,能相对真实地选拔出顶尖的人才。
然而比家长更迷糊的要属年轻的小学生们。他们困惑地发现,学校每次课讲的都很简单,但是一考试就是连题目都读不懂的超难题。以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班为例,老师一个学期才讲一道“五星题”,然而大考时,几乎每一道题的难度都是四星级起步。
“为什么学校要这么干,就不能讲多难、考多难吗?”
实际上,这是中学在进行生源筛选时,所施行的一种“策略设计”。
数学这个学科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少量已知条件推导未知。数学纷繁复杂的定理、公式,都是数学家使用极简单的概念、公理,加以逻辑推导和计算得出的。
而对人进行教育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希望他能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下,利用好已知条件,解决眼前的问题。
而且,数学在锻炼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是最纯粹、最直接的。它不受到任何现象的干扰,只凭借最纯粹、最抽象的数与形,就能做到这一点。
既然数学考察的是人“利用少量已知解决未知”的能力,那各大中学怎么会“讲多少、考多少”呢,当然是“讲简单的,让学生举一反三,解决复杂问题”,并根据各自的表现来筛选出真正的人才。
学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选拔出了“一班、二班”,但那些“三班、六班、十二班”的家长并不愿就此善罢甘休。因为,奥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没有人是为了让孩子变成神童才学奥数的,家长想要的只是重点中学的名额。这完全是生存层面的血淋淋的竞争。
在想提分家长看来,学校“讲得简单、考得难”的策略设计,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把戏。
每个家长都觉得,“我家小孩只是没学过那个知识点,没做过那么难的题,如果他做过,那五星题他也一样做对!”
既然考试者和出题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且这种不对称会影响孩子是否进入重点中学,那么商业力量介入,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来谋取利益,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
奥数课外培训的蓬勃发展,和这种信息不对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学而思、巨人尖子班、精诚学校等机构最早起家的时候,靠的就是强大的教研能力和信息获取渠道,抹平了重点中学“考试”和“讲课”间的信息差。
抽屉原理、鸡兔同笼、数论、囚徒困境……这些极其复杂的中高等数学问题,被高薪聘请的数学名师甚至奥赛教练归纳、总结,再风趣幽默地讲授,让来上课的小学生记住了解决“典型题型”的套路,做题时套进去就好。
但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当奥数成为了“培训”,本质是解构了公立学校“利用少量已知解决未知”的考察策略,把数学思维的考察变成了题海战术。
可是家长却为这些机构叫好,当时还不断有锦旗送进位于海淀黄庄的学而思总部,因为“我家小孩本来什么都不会,在学而思学了奥数,就考进了XX市重点,真的很感谢!”
当奥数培训的口碑传开后,小学生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周六,他们要去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的“坑班”,感受“讲得我都听得懂”的乐趣;周日,他们还要去学而思、巨人学校等课外奥数班,体会什么是奥数真题的难度,并在老师指导下手把手做对原题和变式。
上过辅导班的孩子们做过典型真题,得奖的概率自然就大了。当他们捧着奖状,走进重点中学的时候,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倍感开心。过去吃过的苦,成了“必经的牺牲”。
谁上过课外奥数课,谁就等于提前做过了考试的真题;谁没上过、不知道有这种班、嫌太贵没报名,考试就天然吃亏,甚至一分都得不到。甚至当时很多奥赛名师,就是重点奥数比赛的出题人。
无外乎有业内人称,奥数比赛运行的核心逻辑,就是“明目张胆的作弊!”
国家几度出手禁止奥数,北京、上海、武汉等“奥数”重地,教育局纷纷下重手惩治,然而成果寥寥。既然重点中学招生时永远会问“你们家小孩奥数得没得过奖”,那家长们永远会寻找还在举办的知名奥数比赛、知名奥赛教练私下开的培训班。
至于培训机构,把“奥数班”换个名字,美其名曰“实验班”、“提优班”,其实“换汤不换药”,这都是最最简单的伎俩。
这些机构的存在,着实为家长营造出美好的幻梦:“您孩子奥数不行,来我这儿学,原题都做过,考试怎能不会?有个银牌,那些重点中学都要排队请您去签约!”
人活着,总得有个梦想。
一地鸡毛:2007-2018
2007年,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在第四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痛批国内奥赛的畸形发展模式:‘奥数’学术活动本身并没有坏处,但我们许多拿了金牌的学生,最后成就普遍不如国外的学生,原因就在于许多中学生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数学,在思维上没有创新。我希望中学生能花点时间去思考,尝试研究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数学课题,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北大、清华或国外名校而整天做奥数题。
事实上,数学是做研究,研究的根本是找问题。奥数只训练做别人的题目,而不引导学生去找自己的题目,结果培养出来的金牌得主,学问狭窄,考试还行,思考没能力,在我这里甚至都不能毕业!
也正是在那一年,国家继续出手调控小升初政策。原因是,国家为了给小学生减负,曾出手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结果市场上还有各项官办奥数学术活动给学生“变相考试”。于是,国家延续减负的思维,解放童年,取缔一批奥数学术活动,加大筹码推行就近入学原则,原则上各校不得以择优录取的方式公开招生。
国家的本意不过是给小学生减负,然而在家长看来,各个中学的师资、条件、同学质量千差万别,就近入学,万一派位到附近最差的学校,孩子的一生不就毁了?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奥数为各报纸的社会新闻提供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素材,比如武汉市多次下发文件禁止小学奥赛,但每年报名人数还在增多,年年突破一万人;比如北京市的迎春杯、希望杯被逐步叫停,商业机构主办的“学而思杯”、“巨人杯”奖项也成了中学招生时的有利参考;上海有学者发布调查说,自08-13年来,小学生家庭人均奥数花销从5800元上涨到8400元……
乱象一直继续,一直到2018年,史上最严格的“禁奥令”来袭。这次好像是真的禁掉了,连好未来集团也被迫转型,发力大语文、新英语,向政策示好。
谁也没想到,奥数没了,小升初却更乱了。
迷茫的家长:2018-至今
禁奥令以来,五六年级的家长们更是方寸大乱。
“今年的小升初靠什么招生啊?怎么各个学校连什么时候开放日都含混其词的?”
“还不是害怕被上面说是变相考试吗,一个个都可小心了,谁也不知道靠什么招生!”
“奥数比赛也取消,特长生加分也取消,中学靠什么选拔学生啊?该不会看谁钱多就招谁吧?”
“你没听说现在都面试家长的吗,有权有势有钱的肯定择优录取!还有更邪乎的,我听说有一个女的开服装店的,就是面试时保证,学校的戏剧课她提供全年级服装,就直接被录取了!”
“真是苦了我们这些踏踏实实的公务员了呦……”
在过去,奥数就像是一场赌博的头等奖、一块古人梦寐以求的免死金牌。每个人心里至少有个念想——万一我家小孩得了奥数大奖呢?尽管它如此难以获得,但它摆在那里,就会让无数人前赴后继地行动起来。
其实不只有奥数,十年前,公共英语三级的证书、连续几年春蕾杯的一等奖、北京科普英语的一等奖证书,都很困难,但都能起到同样的“绿卡”效果。家长们知晓了这些潜规则,便驱使着孩子朝这些证书有条不紊地努力着。没成功,也只能自认倒霉。
规则困难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规则不公开、不透明。面对这种事,普通人只能靠脑补。
家长们实际关切的,其实是小升初招生政策的透明度问题。
明明小升初存在选拔,明明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间存在巨大的差值,那采用就近入学的方法势必难以服众。然而,如果允许小升初考试的完全竞争,又会让小学生们陷入无休止的超前学习与考试中去……
奥数“死了”,“活过来”的新生事物里,有“数学逻辑”和“数理思维”。在这个看起来更“素质化”的时代,面对低年级(3年级以下)的学生教教数学思维是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然而,当这帮孩子进入五六年级,也要面临小升初的各项“隐性考试”时,大多数“数理思维班”便摇身一变,和家长商量,还是做题对提分效率来得高。然后,一切照旧。
而真正能够全程坚持培养小学生数学思维的课程,市场上并不多。派爷我前段时间在天使投资人的推荐下,旁听了在望京设点的德泮教育的一堂课。主讲人张老师是台湾知名数学老师,在美国深造,从事小学数学教学30年。
那是一堂低年级的几何课,教室很宽广,学生们全程要用手去触摸几何体、了解他们的性质。黑板上只写着四个字:点、线、面、体。
旁听体验让我十分激动,我以为自己看到了数学思维大众化的曙光。下课后,我和课程负责人聊天,小心翼翼地问起价格,他回复我说,这是京城最贵数学课,年费要一两万,和 vipkid 差不多。
我问他们,未来能不能通过规模化降价?但答案我心里再清楚不过,这个课堂完全是靠张老师对奥数以及课堂的理解在支撑。这种交互性极强的课堂,互联网教育目前无法介入,价格也很难降下来。
贵的教育是不是好,这不一定。但反过来说的话,好的教育,一定是贵的。
1985年,著名艺术家、作家刘索拉发表了一篇小说《你别无选择》。“你别无选择”,这个书名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奥数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根本原因。
奥数早已不是少量天才拓展自我的游戏,而成为每个平凡孩子为了跻身重点中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尽管国家希望“减负”,取消小升初阶段的所有考试,但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让中国家庭无法接受“就近派位”这种无异于“自然死亡”的结果;重点中学也不可能满足于“就近入学”,势必要储备属于自己的王牌尖子生。
国家、中学、培训机构、家长,每个主体都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理性决策。结果,在中国教育这个如此复杂而巨大的体系下,各个主体的利益却彼此缠绕在一起,甚至南辕北辙,这也塑造了奥数如今“不禁真不行、禁了也尴尬”的局面。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是:自1990年以来,中国奥数代表队前后十几次捧得第一名佳绩,已经成为IMO当之无愧的获奖大户。
但是,相比于拿奖路上的“满腔热血”,这二十年来中国对于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或许也只是“一地鸡毛”罢?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