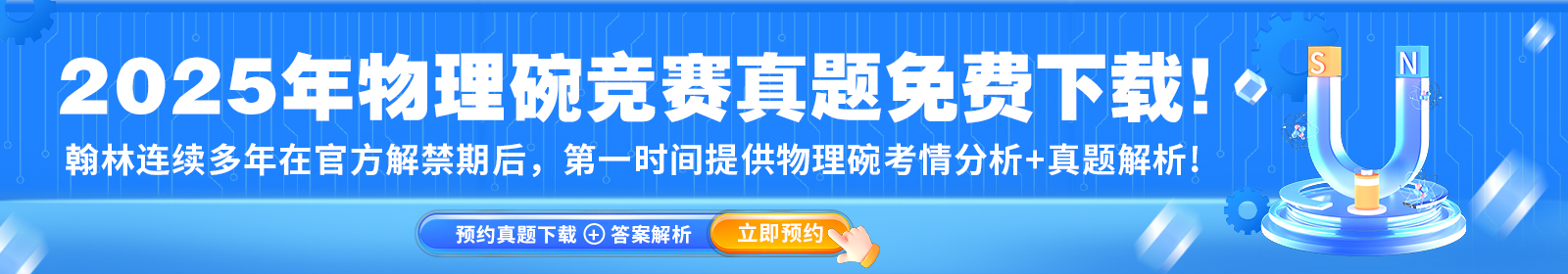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常分享 | 无论底牌多差,总有人凭这把钥匙逃脱基因牢笼
“
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原生家庭环境”对孩子教育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只能尽量多元、全面地来看待它。现在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很小,孩子的绝大多数特征已经被基因决定了;而在本文中,哈佛历史系毕业、现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的魏阳教授则提出了一个比较有人文关怀的观点:“基因”和“环境”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而如果说基因决定了人的生理,那么,教育和社会改良则可以让我们逃出“基因牢笼”。
”
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更多的是由基因决定?还是由社会环境决定?
这个问题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中,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中国,叫做“先天后天”之争。在西方,叫做“Nature vs. Nurture”。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科学研究还没有给出确定答案。
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人的许多特征,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些研究,多基于对同卵双胞胎的观察。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一样的,如同克隆人。所以,观察在不同环境中生长的同卵双胞胎,也许可以了解人的哪些特征来自基因,哪些来自环境。
研究表明,在不同家庭环境中生长的同卵双胞胎,体质、疾病、智商、性格、某些才能、幸福感基本趋同。而同一家庭中收养的孩子和亲生的孩子,在这些指标上和来自随机家庭的孩子,差别不多。
这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人的行为特征时,强调基因的作用,怀疑环境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因,就决定了人的一生。这更不意味着,你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就变得不重要了。“
当我们将基因和环境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其实问错了问题。
”
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人的行为特征,是由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即使是某些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也很难说单纯是基因的结果。如果精神分裂症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同卵双胞胎中有一个得此病,另一个也应该有。
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在相同的家庭,第一胎和后面几胎的弟妹之间,会产生重要行为特征差别。换言之,即使生长在同一家庭的孩子,也没有分享完全一样的家庭环境。
微小的外在环境差别,在正反馈机制下,会产生俗称“蝴蝶效应”一样显著的后果。基因与家庭的关系,比我们以前认为得更复杂微妙。
决定我们生命轨迹的,不全是先天的基因,也不全是后天的社会环境,而是基因和社会环境的复杂互动。
基因多样性与环境:
物种的繁殖,就像赌博,不断突变出各种基因,将它们撒向自然。最终哪一种基因能胜出,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是指多种多样的生物基因,被偶然的环境选择的结果。
而进化的结果,未必是更大、更快、更“高级”的物种。比如,在印尼的弗洛伦斯岛上,古生物学家就发现了史前一种体型很小的大象遗骸。(或者应该称之为“小象”?) 在与大陆隔绝的小岛上,为适应资源的稀缺,这里的大象进化得越来越小,即使成年后,身高还不到现代亚洲象的一半。
小岛上还生存过一种早期直立人,是我们人类的近亲。由于环境原因,他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米1,被称作“霍比人”。更小更慢更“弱”的物种,在特殊环境中,也可能更好地适应自然。所以,进化不等于有固定方向的“进步”,而只是适应多样化的环境而已。
文化的多样性和基因:
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不输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
基因的丰富性,让人的性格和才能也同样丰富多彩。然而,最终哪一种才能可以脱颖而出,还得看这基因碰巧生在怎样的社会文化中。在不同的环境中,相似的基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表现。
- 一个在中国科举时代能将古代经典倒背如流、提笔成章的书生,如果生在连文字都没有的游牧部落,他的才能将一钱不值。
- 一个能把棒球投出每小时100英里以上速度的神童,在现代美国,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棒球巨星;同样的基因,如果生在中世纪的欧洲,连球都不摸着,只是个路人甲。
基因决定的才能,仿佛一粒骰子,被撒向你碰巧生存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在基因和环境互动的老虎机中,摇出你的命运。
如果性格主要由基因决定,那么什么性格更适应社会环境,也可能是偶然的。
- 生于乱世的枭雄,大胆冒险的性格也许让他功成名就;
- 在制度礼法严苛的年代,同样性格,却可能葬送一个王朝。
开拓与守成,需要不同的领袖人格。
不爱铁饭碗,喜爱创新冒险的性格,在六十年代中国单位体制中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因为投机倒把而被枪毙。而同样不安现状的性格, 在改革开放后,却能如鱼得水。八十年代第一波下海发财的,往往是在原先国有体制下,最被边缘化的那些人。
原来混得差,未必是因为基因“差”;而反过来说,现在混得好,也未必是基因“好”。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是因为基因和环境的复杂互动。仿佛浅水塘里那一大群青蛙,哪一只活得更欢,还得看那一年老天爷碰巧赏的雨。
所以《老炮儿》里的冯小刚感叹:
谁没个点儿背的时候呢?
这里说的“时候”,就是中国古代“时”的观念——所谓“时势造英雄”。有时候,基因再牛逼,也会走投无路——正所谓英雄末路。有时候,基因再糟糕,含着金汤匙出生,总能出人头地——正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所以,当我们将基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其实问错了问题。就理解人的行为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去考察基因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呈现,社会环境又是如何作用于基因。
用英文来说,不是Naturevs.Nurture,而是NatureinNurture——不是“与文化相对的基因”,而是“与文化相交融的基因”。
“
凭着教育和改良,我们走出基因的牢笼。
”
这一结论,让我们重估两个观念。
第一,是重新理解教育的本质。
如果智商、性格和幸福感是由基因决定,后天无法改变;那么,教育将是一种在不改变基因的情况下,让人类更能适应环境的社会调节手段。
- 从第一块石器到第一把的铁器,人类花了大概两百万年;
- 而从第一把铁器到第一杆火枪,人类仅仅用了两千年。
文化,让我们不必再等待基因的改变来完成漫长的进化,而可以迅速适应自然;不仅适应了自然,甚至让自然来适应我们。在过去的一万年中,人类的行为只能从其基因在文化中的表现方式,才能加以理解。
教育,就是在不改变个体基因的情况下,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对知识分享,让人类更好地适应环境的自我调节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延续,完全依靠教育的成功与否。
教育的存在,正是为了弥补基因在适应环境方面的不足。
当代教育的目标,依然是通过文化的熏陶,让个人迅速适应一个变化的社会。这里的教育,包括了家庭、学校、社会和自我的教育。这些教育经历,无疑将对你的人生,发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那些基因看起来不适应目前社会环境的孩子,这一机制尤为重要。研究表明,有些所谓“基因缺陷”,只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中,才成为“缺陷”。
比如注意力缺乏多动症(ADHD);这种“基因病”在需要不断奔跑攀爬的采集狩猎社会,不是一种病态,反而可能有进化上的优势。只是在文明产生后,在崇尚服从、安静、和课堂教育的现代教育体制中,才成了大人眼中的病态。
特殊教育的目的,是让那些基因未必适合目前社会环境的孩子(比如有自闭症,注意力缺乏多动症,或其他先天缺陷的),也尽可能融入社会,活得有尊严。
这带来第二个需要重估的观念:社会改良。
哥伦比亚大学的姜纬教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年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们说到:
“当你觉得自己能力超群的时候,要同时认识到你所具备的能力恰好在当今当地具有很高的市场赋值。这就是你享受的优越条件,或是运气。”
如果个人的成功,只是偶然获得的基因,与偶然的社会条件交织,产生的偶然结果;那么,这种成就,当然含有极大的运气成分。既然获得“优秀的基因”和顺利的社会环境,两者皆是运气,你实在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藐视他人。
因为,那些沦为弱势群体的“失败者”,可能并非由于懒惰和愚蠢,而可能只是运气稍差没有获得“优秀基因”,或者只是因为先天条件碰巧不适合当前的社会需要而已。他们只是没有你的好运:在一个合适的时代,拥有合适的基因。
换句话说,也许改变一些社会条件,让机会更加平等,阶层更加开放,这些运气不好的人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走得更远。
一个良好而公正的社会制度,能够让更多的人充分发挥基因中的各种天赋,不浪费自然给予的每一份礼物。
提高我们利用人类基因的效能,是和利用自然给予的其他资源同样重要而紧迫的事情。为了不浪费基因,则必须、也只能通过改良社会体制;让社会弱势群体的基因资源,也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在这方面,我们还离答案很远。
人类的文化,让我们在面对来自环境的挑战时,不必像其他物种一样听天由命,仅凭基因的多样性存活。文化,让我们利用教育、创新、和社会改革等机制,选择最好的发展方式,迅速适应并改变环境,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快乐——哪怕是有着基因缺陷的个体,也能凭着教育和改良,走出基因的牢笼。
如果基因塑造我们的生理,文化则让我们获得自由。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