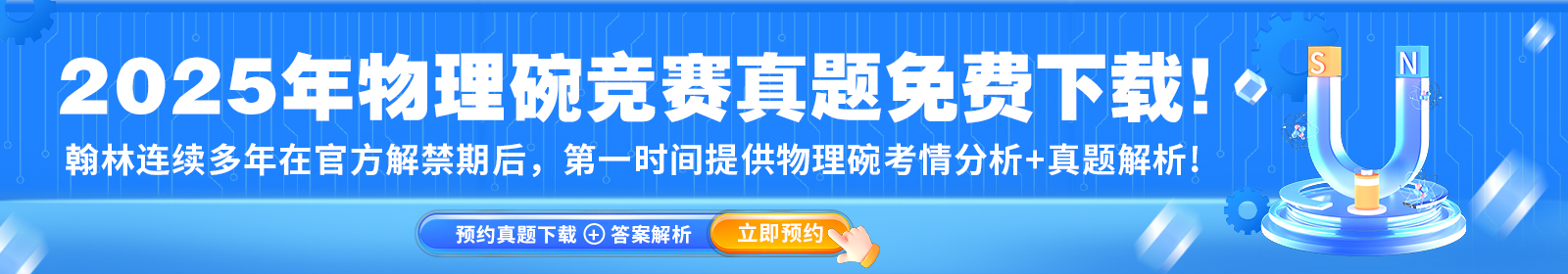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四)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一)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二)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三)
04
灯光,在隧道尽头
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从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阅读课时找到研究题目到2009年论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译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出版,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
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
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写博士论文时碰巧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时代四部曲”(国内译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我虽然算不上左派,却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觉得社会学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几乎有了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不过后来找工作时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虽然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折腾了半年时间,但最终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教职,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这几年来,我对写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尤其想写1979-1989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话,还要感谢这次彷徨的经历。
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
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
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赵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两侧,而他自己则面对着我坐在窗前。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窗口还是紧闭着,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
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来源:管理学季刊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