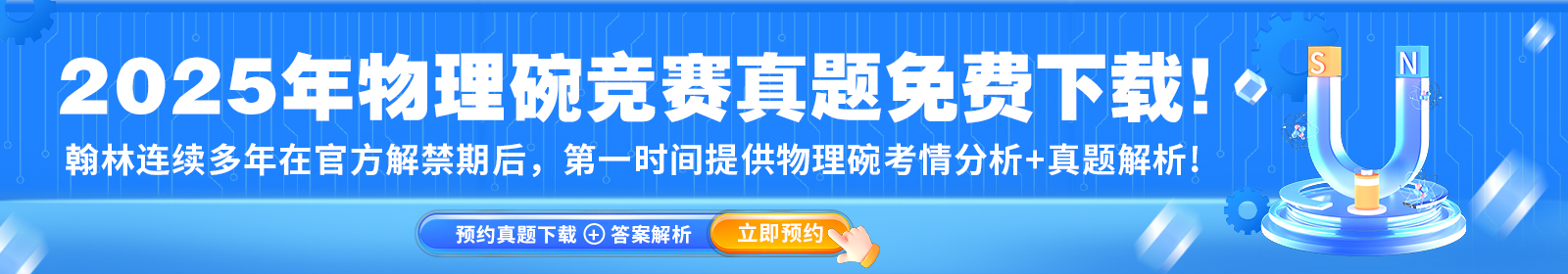- 翰林提供学术活动、国际课程、科研项目一站式留学背景提升服务!
- 400 888 0080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二)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一)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三)
我的博士生涯:"活着"走出了世界高校学术训练最严酷之一的地方(四)
02
阿伯特教授
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美国的学校里师生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会亲切地直呼老师的名字,但他从不允许系里的学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当然,他对学生也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去办公室见他时,他张口就是“刘先生”,后来熟悉了之后才开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从芝大毕业到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来的对匿名评审人的感谢信,结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写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思达,你现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过,至今为止,我还总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养成的习惯,哪有那么容易改过来呢?
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书都认真读的话,人一辈子最多也就读一万多本书而已,书再多的话就只有收藏的意义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里,其实前者比后者难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结果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
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
不过说来也怪,我从在芝大的第二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也就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再做一份书单,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法律职业,所以两门阅读课都是关于职业社会学的,两个学期读下来,让我不但彻底精通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论文的理论突破口,也就是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学徒式”的阅读课,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最好的方式。
许多过来人都说,博士读的时间长了,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不只是学术观点,有时连发型、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所谓“为人师表”,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有只“教书”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当然,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比如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结果他说,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纪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样东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马力”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迄今为止,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最有道理的话,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
说阿伯特教授不关心学生,其实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罢了。比如我这辈子讲的第一节课,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学期,选了他的一门叫作“行动与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课——芝大的教授经常会开一些稀奇古怪的课程,比如这门研究生课,他似乎只讲过这一次,只有六七个学生——结果没想到,刚开学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岁的父亲就生病了,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从波士顿给我写邮件,说自己赶不回来了,因为我是班上年级最高的学生,让我代他组织大家讨论。我看到邮件后即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把要讨论的阅读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课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气氛也很融洽。有了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教学经历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以后无论在哪里讲课,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
阿伯特教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即使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要穿长袖衬衫,有时还会戴一顶草帽,很有复古范儿。我在芝大期间,只见过一次他略显邋遢的样子,那也是某个冬季学期的第一节课,阿伯特教授走进教室时,我和同学们全都惊呆了——平日里衣着光鲜的他,头发蓬乱着,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个幽灵。然后,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地告诉大家,他圣诞节之前被诊断出了癌症,刚刚做完手术。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手术之前他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大部头的社会理论书还能不能完成。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继承人,他的手术很成功,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太忙了,那本书至今都还没写完。
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极其纯粹的追求。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进的学者,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甚至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但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演进,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

早鸟钜惠!翰林2025暑期班课上线

最新发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2023009024号-1